你好,我是顾衡,又到这周的互动时间了。
本周,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杰夫·谢索的《至高权力》,讲的是福兰克林·罗斯福与最高法院围绕新政的一场权力缠斗。
可能是因为在这本书之前,已经介绍了杰弗里·图宾的《誓言》,大家对美国最高法院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留言里谈感想的就多,提问的就少。不过还是有几个不错的问题。
"有一种声音说,以非民选的法官的判决宣告民选的国会的法律(违宪),本身是反民主的。总统任期最多不超过两届,参议院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每六年改选一次,法院的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就可能任职终身。若国会与总统发生争执,可在短期内因总统或国会改选获得解决,而法院与其他政治机构之间的争执则可牵扯到相当长时间。法院极易限制其他机构的行为。顾老师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段话挺长的哈,简单总结其实就是,有种观点认为法官因为是终身制,所以极易限制其他机构,也就是白宫和国会的行为能力。
我是这么看的。首先,以非民选的法官审查民选的议员通过的法律,本身是反民主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美国设立最高法院的初衷,就是要用专业的司法机构来制约民主。
古雅典搞直接民主制,什么都投票。遇到案子就随机抽选陪审团。也就是说,雅典缺乏专业的司法机关去制约民主。这样的民主机制下,处死了苏格拉底。
还有别的例子:公元前406年的阿基诺萨海战中,雅典海军战胜了斯巴达海军。仅仅因为风高浪急,没有及时打捞本方士兵的尸体。六名海军将领被投票处死。另外,古雅典人还有臭名昭著的贝壳放逐法。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弊端,所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民主制,评价都不高。
那么到了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是不是民主就不再需要,或者就不那么需要法制的制衡了呢?仍然需要。因为,民主是按人头的。政治家为了当选,就必然要迎合民众。而这种迎合是危险的。
为什么说它是危险的呢?有三个理由:
- 第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等于全体人的利益;
- 第二,就像勒庞说的,群体的智力与其人数成反比,由投票产生的政策,往往并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拉美此起彼伏的民粹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过些天我会介绍一本书,叫《掉队的拉美》,会详细谈到拉美的民粹问题;
- 第三,数人头的民主,还往往会侵犯少数人。
所以,托克维尔说,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政治家与民众之间距离危险地丧失”。这个距离感,靠政治家的自觉是行不通的。因为投票规则本身就决定了他对民众必然是迎合的。这个距离由谁来保障呢?只能靠法制。
回到你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的设立,初衷就是他们为了保持民选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而这个距离感,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大法官被任命时,基本都是50多岁,干到70多,平均任期就是20年,历经五任总统。九名大法官,9除以5是1.8,也就是说,只要一届总统运气不太坏,他总有换两个大法官的机会。
即使大法官与任命他的总统一直保持一致,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也不过就是最近五届总统政治倾向的平均。这个平均,其实是保证了美国很多政策的延续性,避免因为换了总统就发生政治政策剧烈摇摆。
所以,最高法院确实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就像前几任总统阴魂不散一样。
但是要说这个滞后有多么严重,我也不这么认为。如果20年间有两任美国总统连任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三任总统的加权平均。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滞后程度。
就拿《至高权力》这本书来说吧,当时的首席大法官休斯就说:
慢一点,稳一点,从长远来看,作为一种长期的策略,是更可取的。
所以,我对你提到的那个声音的回答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最高法院就是反民主的。如果不反民主,要它干嘛呢?说到它对其他两个机构的制约,从程度上来看,我认为刚刚好,并没有过分。
"各国总统虽然不能说是国内最顶尖的人才,但最基本的政治修养应该是有的,而且他们肯定都有一大群幕僚吧,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罗斯福应该不缺专家,他为什么还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以后的政策,你们最高法院帮我审审呗”的要求呢?"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不过可以猜猜看。总统确实并不缺幕僚。但是幕僚也得总统问了,他才有机会提出建议啊!罗斯福写封信找个人交给最高法院,如果他事先没问他的司法部,没问政府雇的律师,那这些幕僚就没有机会拦着他干这件蠢事儿。
也正是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罗斯福虽然是个律师出身,但是确实缺乏一个律师的起码素养。他以前律所的合伙人对他的评价是没错的,就是,罗斯福要是想吃法律这碗饭的话,混不出啥名堂。
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之前干过这事儿的总统只有华盛顿。刚建国嘛,大家都搞不清楚。也正是华盛顿那次,大家才确立下来最高法院只有事后审查权,没有事先的建议权这么个规矩。时间隔了100多年,罗斯福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先例吧。
"“连续内共生”理论的作者讲到了人整合了细菌和病毒才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越来越依赖的手机、智能手表,算不算第二次整合?我自己就很想在体内安装一个芯片,来监测身体、接收和发出信息等。另外,如果“连续内共生”是一种人为进化的方式。那么,在哪一次整合的时候,我们开始被称为“人”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手机和智能手表,以及埋入体内的芯片,算不算整合?
我觉得算吧?咱们介绍的第一本书《技术垄断》里,就讲了麦克卢汉的“主动完成”和“结构冲击”这两个大词。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工具是如何“整合”人类的认知和行为的。这个例子就是钟表。
有钟表之前,人们并没有时间可以被分割的概念,也就不会有按时间出售自己劳动的想法。现代人雇个小时工,不管干多少活,一个小时都要付35块钱。这在没有钟表的古代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只接受按劳动成果付费的交易。如此一来,一些无法以可见物作为成果的劳动,就得不到报酬。这是古代人智力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不要说手机了,简单的一个钟表,对人的行为和认知模式就产生了如此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说人与工具是一种整合关系,我认为完全是成立的。甚至不用有个芯片埋到体内的这个动作。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人是什么时候被称为人的?这是个生物学概念,就是生殖隔离。就像马和驴交配,能生出骡子。但是骡子没有生殖能力。从这个点 ,马和驴就被分离为两个物种,也就是说,马成为了马,驴成为了驴。
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例子来,正好说明高等生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有多么重要。就是生物学家多布然斯基曾经做过一个果蝇实验。他把一群果蝇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在25度环境下培养,一组在27度环境下培养,这么繁殖到第25代之后,两群果蝇再交配,生出的后代就已经没有繁殖能力了。
分析发现,这两种果蝇的区别,仅仅在于肠道菌群分布有所差异。你看,与不同的细菌产生共生关系,对高等生物就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好,我是顾衡。欢迎各位继续提出优秀的问题,咱们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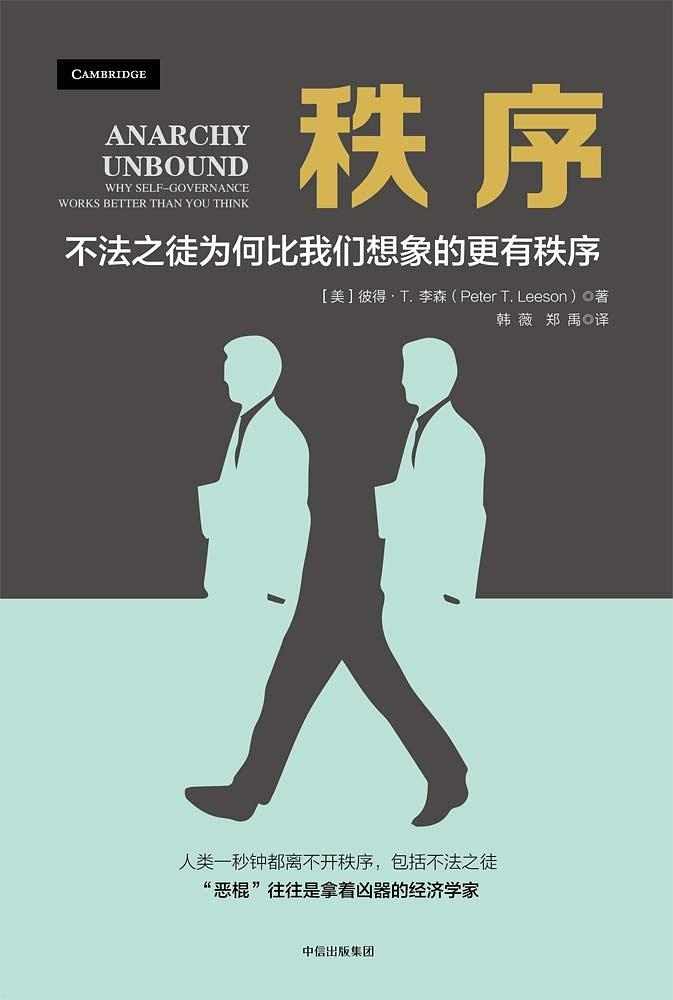
《秩序:不法之徒为什么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秩序》
[美]彼得·T.李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