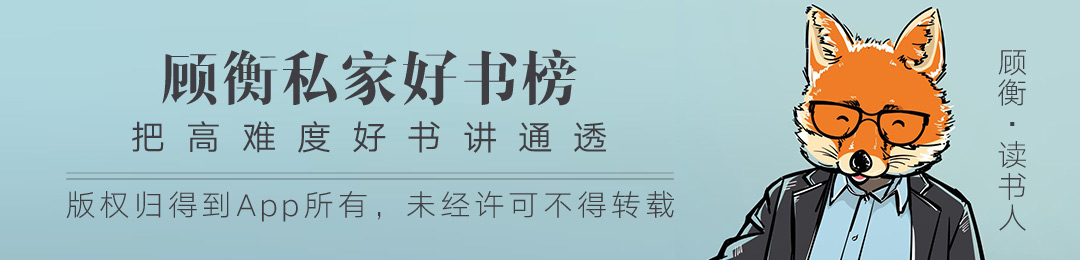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又到周五聊天的时间了。
本周,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彼得·李森的《秩序》。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有一个政府才是划算的,以及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可怕。
这个星期留言区最热闹。看来这本书挑战了很多人的认知,也可能很多人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一个国家贴近自然生活的状态,比如原始部落的状态,那么无政府状态会比有政府好,然后等文明程度增高了,出现了比较细致的分工,那么出现政府就是必然的,即使运营这个政府的成本会很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可能弄反了。很抱歉我无法想象一个根本无政府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蓬蓬同学其实提了好几个问题。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不是原始部落,无政府比有政府好?是的!这确实是李森的观点。为了解释这个,他还弄了个H-L与G比大小的模型嘛!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文明程度提高了,出现了比较细致的分工,那么出现政府就是必然的,即使运营这个政府的成本很高?
这更像是洛克的观点。李森不同意这个观点。李森认为,即使文明程度提高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社会有政府也并不是好事。他举的例子就是索马里的军事独裁政府。不过还有一个例子是比利时。比利时因为政府破产停摆了541天,也没出什么乱子嘛!没有政府的国家,不需要你想象,看看索马里和比利时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在非洲的老祖宗不算,单从走出非洲开始算起,也有20多万年的时间了。但是政府,最乐观地看,也只是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仅仅从这一点看,霍布斯的“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的假设就是不成立的。
李森这本书,其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讲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就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现代人,不能只享受互联网和高铁这些现代经济文明,也要享受现代政治文明。
而对于现代政治文明而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命题。所以关于这个话题,我还准备了《国家的视角》《伯林传》《秦汉帝国》《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秩序的根基》这一组书,从各个方面来继续讨论它。
我非常感谢你,在面临一个自己之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时,还能保持如此开放的心态。我也相信,在听完这一组书的介绍之后,你会对两种秩序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全面的理解。
"本节讲了没有政府也能产生秩序,但是必须要有惩罚!但是我的疑惑是,这个惩罚的执行和推动也是由这个民间“草包”的组织来做的。这,是不是也相当于一个小政府。按这个逻辑推导,其实李森说的自下而上的秩序,是不是霍布斯说的利维坦这种我们熟悉的大政府的前身和由来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笨小孩一点儿都不笨,他总结出了李森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不管哪种类型的秩序,它都离不开两个字:惩罚。那么,小尺度的、通用于熟人社会的惩罚,是不是利维坦的前身和由来呢?
恰恰相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秩序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前身和孵化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两种秩序的不同。比如,小区里有人种玫瑰,因为玫瑰好看。而妈妈们则不喜欢,因为玫瑰有刺,会伤到孩子。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如果一个妈妈是喜欢利维坦的,她会征集足够多妈妈的签名,要求议会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种植玫瑰。也就是利用妈妈人数比喜欢玫瑰的人多,来形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迫。如果她成功了,小区里就没有玫瑰了;如果她不成功,则她的孩子就得不到任何保护。她只有这两种可能。
可是如果她采用协商的办法呢?比如她组织起小区的妈妈,与玫瑰种植者一起开会。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是存在的。比如,玫瑰种植者同意在玫瑰外面种几排小叶黄杨,来保护孩子。如果他不种这个隔离带,则孩子受伤的话,玫瑰种植者承担一半医药费。诸如此类,可能的结果会有很多。
协商一旦形成了结果,它不仅不是利维坦的前身和由来,反而是对利维坦最有效的抵抗。
在这个例子中,甲主张他有在小区里种植玫瑰的权利,乙主张她有保护孩子在公共区域不受伤害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是彼此矛盾的。那么,谁有权,谁没权,各自的权利边界在哪里。划清这个边界,有两种途径。
事实上,我们所有人所有权利的获取,都只有两种途径:法律授予和当事人合意。法律授予你权利,这个是自上而下的;而当事人合意,则是自下而上的。我们能够达成的当事人合意越多,对法律的要求也就越小,从而也就更好地保护了社会的多样性。
之前我们在讲《誓言》的时候提到了“司法谦抑”,同样的道理,就是要为当事人合意预留足够多的空间。
那么,自下而上的秩序,也就是当事人合意,有没有能力对违规者进行强制和惩罚呢?当然有!比如,条约可以规定,如果玫瑰伤到孩子而玫瑰的主人不肯付医药费的话,那么孩子妈妈可以拔掉他的玫瑰,孩子妈妈也可以高声叫骂,当众羞辱他。这都是他违约后要支付的代价,也都是惩罚。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自行的法就不应该立出来,您怎么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强调一下。张君威同学问的是“应该不应该”,而不是“有没有”。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二者之间的差别。
前些天我就和一个人有过一次争论。那场争论很无厘头。我认为法律应该是由禁止性条款构成的,也就是“我禁止你做某事,否则我就要惩罚你”。而那位朋友说“古今中外的法律里到处都充斥着宣誓性条款,可见你在胡说八道”。我实在是难以理解,“应不应该有”和“有没有”,是怎么成为争论的两极的。就好比我说“男人不该打女人”,他说“不对,我爸就打我妈”。然后呢?然后就得出“女人该被打”的结论了么?
很多争吵,其实是源于没有耐心倾听对方,以至于误解了对方的意思。吵起来之后呢,面子上又下不来。然后就关公战秦琼,一地鸡毛了。
回到张君威同学的问题。关于“不能自行的法不应该出台”,咱们中国的荀子说得最好。他说:
得其人,就是得到百姓认可了,法律则有用;失其人,就是老百姓不认,那么法律即使颁布了也没用。比如美国的禁酒令,民众不认可,政府失去了威信和税收,得到的却只有羞辱。
和荀子想法类似的还有边沁。边沁也认为,“如果一个法律不被人们普遍认同,则不具备效用”。他进而认为,为了让法律有效率,就不得不以妥协和道歉的姿态,允许观念共识(道德)以杂质的身份进入法律。
但是,虽然荀子和边沁都同意“得不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法无效”。但是在这样的法应该不应该出台的问题上,两个人的观点却是不一致的。
荀子的看法是不应该出台。因为违反人心的法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社会的道德共识,造成礼崩乐坏的恶果。边沁却是以“道歉和妥协的姿态,允许道德观念共识以杂质的身份进入法律”。边沁向什么道歉呢?又为什么道歉呢?因为他为了法律有用,不得不同意让道德“污染”了法律的原则。所以,他是在向法律的原则道歉。
那么,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律的原则与道德观念无法实现完全的重合?
按照英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罗伯特·萨格登的观点,道德不过是基于偶然而形成的社会观念共识。有的道德观念的背后,有道理可讲,有的则没有。但不管有没有道理可讲,只要观念共识形成了,也就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为约束,并且也成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道德观念,是允许彼此之间矛盾的,它也是允许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的。
虽然在实际层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条文与条文之间不存在bug;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在具体操作层面能做到一视同仁。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人们接受道德观念内在的不自洽,而不接受法律体系内在的不自洽。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必须向往之。
没有bug的法,西塞罗认为只能来自于神,他称之为自然法。而人制定的法律,是一定有bug的。可是,神的法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实际上并不存在。
按照西塞罗的看法,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在一个一个的案例判决中,去不断逼近和揭示神意,去追求这个没有bug的境地。这个,就叫衡平。衡平的本质,无非就是让具体的法条变形,以实现对法律原则的追求。
比如杀人偿命,这是法律中的一条原则。可是万一船失事了,咱们六个人在一只木筏上漂着,都要饿死了。这时候,大家都同意用抓阄的办法,把一个人杀掉吃了呢?这么着,我不幸被你们吃掉了,你们五个活着到了岸上。按照道德的观念,你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自我存活为目的,而牺牲他人的生命。你们五个非常不道德。
但是法律会怎么判呢?法官很可能会判你们五个人死刑,来迎合道德观念。然后,再以紧急避险为由,判你们在监狱里待三个月,并赔点钱给我老婆孩子,也就算了。法律眼里的善,是只死一个人比六个人都死了要好,法律眼里的善,也考虑抓阄时的自愿和程序的公平。
回过头来看,“不能自行的法”,体现的是人们对应然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应然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不能由道德说了算。因为道德不过是人们在实然的世界中达成的观念共识。如果我们以“能不能自行”来为法设定一个牢笼,人类就丧失了精神的超越性。
虽然休谟早就提醒过我们,“人类无法从实然推导出应然,也就是无法从真推导出善”。但是,我们要把“应然的善”理解为西绪福斯的那块石头。人活一辈子,应该是有点什么东西,是拒绝被功利这把尺子衡量的。
好,我是顾衡,这期就讲到这。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