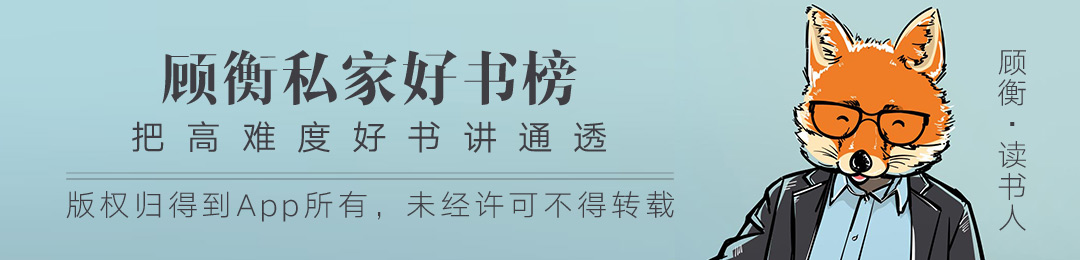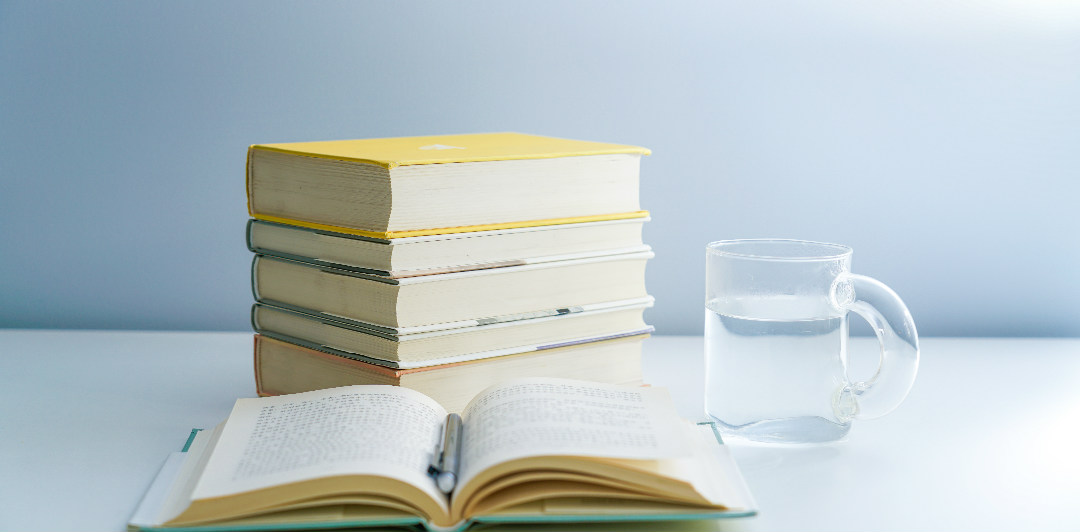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这一期节目,再为你介绍几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一《哗众取宠》格雷森·佩里
这是一本讲当代艺术的书。佩里是伦敦艺术大学的校长,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
关于如何理解艺术,尤其是如何理解当代艺术,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佩里这本小书虽然没说让我拨云见日吧,但还是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
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这三者如何区分呢?我从佩里这本书中得到的启发的是,看他们为谁而画。
所谓古典艺术时期,其实就是订制时期。和贵妇找裁缝做付手套做一顶帽子是一样的。裁缝在动手做之前,就知道是为谁而做的,会得到多少收入,以及顾客关于质地、大小和样式的各种需求。也就是说,设计方面,主要是人家顾客拿主意。
绘画也是这样,英国另一个艺术史学者巴克森德尔专门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合同。他发现,即使是拉斐尔的圣母像,画什么题材、画多大、画几个人、是站着还是坐着,合同里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那个时候,大家还把画主要当作一个工艺品来看待,这么着,就很在意材质。觉得一幅画之所以贵,主要是因为用的材料贵。于是,合同里除了画的大小、构图的复杂和简单、画几个人之外,关于用多少金线,以及昂贵的颜料用在圣母袖口还是脚上的鞋,都有严格的限定。
那么,什么是现代绘画呢?其实就是大卖场。
博马舍发明了百货商场,裁缝们不用等贵妇上门了,没事儿就做大路货吧。做好了往百货商场一堆,让大家随便选。绘画也同样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就是,画家先画,画完了等客人来挑。那客人喜欢什么呢?光靠瞎猜可不行,只能紧跟时代潮流。
那这个时代潮流由谁来制定呢?那就是控制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来制定。所以,现代绘画,本质上不过是各种哲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具象化而已。比如印象派与实证主义哲学、野兽派与伯格森生命哲学、表现主义与自由意志、超现实主义与精神分析。至于象征主义和达达主义,那跟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更加密不可分了。这些名词和流派,你不太熟悉也没关系,我就是举个例子。
而当代艺术呢?当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在于,它的销售对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它不再针对广大中产阶级了。如此一来,艺术家与报纸杂志和电视这些大众传媒保持良好互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代艺术的顾客变成了公共机构、私募基金、收藏家。需要注意的是,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兴起,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就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垮台之后,货币失去了锚,各国都滥发纸币,艺术品成了保值储值和升值的重要手段之一。
从那以后,艺术品,既不指向审美,也不取悦大众。它成了一个特别脱离群众,也特别脱离现实的东西。
那么,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既不炫耀技巧,也不以唤起基于审美为基础的情感共鸣为责任,更不取悦大众,那怎么说服有钱人产生购买呢?换句话说,怎么向买主证明它作为一件艺术品,拥有良好的品质呢?
佩里总结的几条特别好。
首先,你要过得了同行评价这一关。因为现代艺术,已经从技艺演变成了一项复杂而精巧的概念。它好还是不好,是不能由观众来评判的。就像音乐,《小苹果》最热,但就音乐品味而言,它是滥俗的,是没有长久价值的。而收藏家买艺术品,在意的并不是现在的价格,而是它100年后可能的价格。
其次,是策展人。策展人通过把一件作品在哪里展、和谁一起展,来标定这件作品的价值。就好比你做了个服装新品牌,你把专卖店开在GUCCI旁边还是优衣库旁边,那身价差别可就大了去了。
第三,经纪人决定把你的作品卖给谁,这个也很重要。福特基金会来买,5块钱;火车站倒卖火车票的王小二来买,多少钱也不卖。用这个办法,告诉收藏家,你100块买的话,以后会升值。
最后,就是专业杂志了。既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关于概念的游戏,那就要建立起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观念谱系。
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当代艺术的工作做得并不好。你听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聊哲学,和听村头小卖部翠花婶聊弗洛伊德没啥样。三句话之内就拐到算命上去了。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收藏家也不真的在乎你都说了些什么。
这套机制,表现怎么样呢?
截止目前,我觉得运转良好。当年曼佐尼把自己的大便装在罐头里,按当时黄金的价格,每罐净重30克的大便,标价37美元。现在,这些大便罐头比黄金贵了250倍。只要有钱人高兴就好。
当然,佩里这本《哗众取宠》,说的可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内在的销售逻辑这一件事儿。它也探讨了艺术的边界问题、艺术与大众的关系等等。也可能是当代艺术方面的书我看的并不多。但这真的是一本我能看得下去,并且看得津津有味的一本。
二《观念的市场》路易斯·梅南德
买这本书是因为目录里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大学教授的想法都相似,这个吸引了我。
一看,还真是讲到了美国大学政治倾向的偏好问题。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教授中,理工科的还算正常,支持民主党、支持共和党的,比例和大众偏差不大,文科教授就邪乎了。2004年,共和党小布什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是顶级大学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教授,投小布什票的统计学比例为0。
索维尔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里也提到了这个偏差,不过他提的是小布什四年前的竞选。2000年,顶尖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投小布什的统计学比例也是0。
对于这个现象,梅南德的解释是,在美国,有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偏向自由派;有可能现在当教授的,正是婴儿潮那一代,年轻的时候就激进;也可能是大学教授习惯于对现状提出质疑,所以保守派就少。
我觉得这梅南德自己就是哈佛英语教授有关,对这个现象的批判和揭露远没有索维尔那么严厉和深刻。
相比之下,索维尔的批评我觉得就直指本质了。他说,美国的文科教授们,他们并不像物理学教授那样,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物质;他们也不像经济学家那样,研究的是怎么赚钱。文科教授们的工作对象是理念。
那么,当他们的结论越是经不起现实的检验,他们也就越是拒斥这种检验。从而在一种自偏离中实现了自强化。也就是说,越是不能用来解释和指导现实的学说,反而越是安全。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在美国,处理观念的知识分子,可以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愚蠢,并以此洋洋自得。他们用不屑于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假清高,来掩饰自己无法解释现实的无能。
不过梅南德没有回避一个真问题,也就是,在美国高校中,民主党人形成了这样的气候,保守派立场的学者,在大学里会不会受排挤。也就是所谓的,选择偏差。
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大学教职这东西,讲究师承。左派导师收一个右派立场的学生读博士,就已经是小概率了,毕业后来推荐留校任教,这几乎就不可能。所以,学术自由只是台面上的东西,亲近繁殖却是触目惊心的现状。
这本书还讲了其他几个问题,比如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等等。
其中有一个问题说得很沉重。就是美国的大学学费越来越贵,但是这张文凭却越来越不值钱。这说的是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你的收入并没有高出多少。甚至蓝领白领还倒挂。那么,从产品的角度,从生产的角度,大学这个机构,为社会、为学生,提供了什么?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我觉得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如果你对教育这个话题有兴趣,那这本小册子值得你看看。
三《规模》杰弗里·韦斯特
杰弗里·韦斯特是个物理学家,本来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负责高能物理项目的。但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把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给砍了。那他就想,生物学以后肯定是热门,他就把兴趣转到生物学去了。
当时他的想法是,我物理学多牛啊!科学王冠上的宝石。你们生物学美好的明天终于来临啦,我韦斯特来降维打击你们啦!当时,他的想法非常朴实,就是,为生物学写方程。
方程倒是写了一个,叫“规模缩放效应”。就是这本《规模》里讲的东西。这个公式是:规模每扩大一倍,便会产生25%的节余。
但是这个公式并不是韦斯特发明的。早在1932年,瑞士生物学家克莱伯就发表了论文。说“各种动物的基础代谢率,与体重的3/4次幂成正比”。
这个“3/4次幂”是什么意思?韦斯特在书中举的例子是:大象体重是老鼠的一万倍(104),那么,大象的代谢率只是老鼠的1000倍(103)。也就是说,一个大象细胞,代谢率只有老鼠细胞的1/10。
在生物界,体重与心率、呼吸频率、肺泡总面积,以及植物的叶子数、枝条数……相同的规则无所不在,也就是体重增加一万倍,相应的功能只需要增加1000倍就好了。
不光是在生物界,在人类社会也存在这个规模缩放效应,就是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万倍,那下水道、道路、电线这些市政基础设施,只需要增加1000倍就好了。也就是说,人头平均下来,设施投入可以节省90%。
韦斯特离开物洛斯阿拉莫斯之后,进入了圣塔菲研究所,还担任了所长。圣塔菲研究所,听说过的就知道,这是研究复杂科学的圣殿。
它成立的初衷,就是认为用还原论的方法,也就是写方程的办法,解决不了复杂问题,需要有颠覆性的方法论出来才行。从这一点来看,韦斯特作为一任圣塔菲研究所的所长,就捣鼓出这么个玩艺儿出来,是让人失望的。因为你还是企图以写方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然后你抄了个别人的方程。
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当年,圣塔菲研究所都在关注些什么问题,你才能理解这个机构是多么具有前瞻性。这方面的书,我推荐布莱恩·阿瑟写的《复杂》。(有好几本书都叫《复杂》,我推荐的是布莱恩·阿瑟的那本。)在这本书中,你尤其关注一下考夫曼和荷兰德这两个人。
韦斯特这本书,也算是开卷有益吧。毕竟解释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关于大城市好还是不好的争论,这本书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这几本书就介绍到这里。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