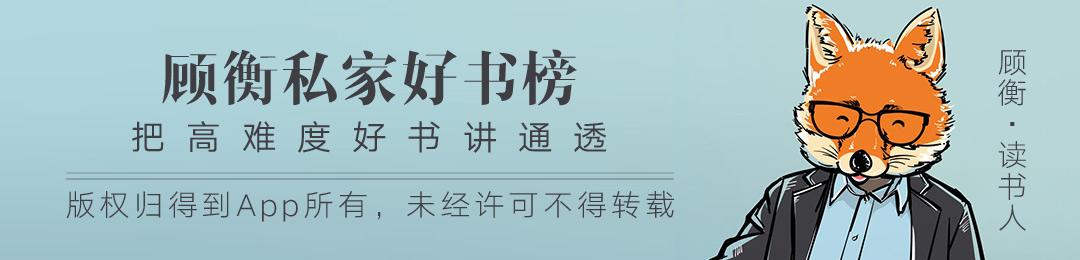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昨天,我们介绍了两种秩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主张政府管一切;一种是自下而上的,主张政府克制,为市场机制、为微观的自治留出空间。
要注意的是,就算是主张自下而上观点的,也没有激进到说政府可以不要了这样的程度,毕竟洛克自己也认为政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传统上,大家都认为,政府还是得有。自下而上的秩序,只适用于小范围的、同质的人群,只是政府的一个补充而已。
但是彼得·李森就比较激进。他的两个核心观点是:
- 第一,在人口众多、社会群体多样化甚至互相敌对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产生自下而上的秩序;
- 第二,自下而上的秩序,并不仅仅在小范围才管用。即使范围扩大到一个国家,也仍然可以建立起来,也仍然管用。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第一个观点:自下而上的秩序,即使是在远距离、彼此敌对仇视的群体之间,也仍然可以产生。
第一个例子:安哥拉商队与部落贸易
李森的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
大连这个地方,盛产樱桃。关于樱桃的生产,你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果农把樱桃树种在大棚里,大棚都是一样大小——每个标准棚1000平米,也就是一亩半大小,里面有100棵樱桃树;第二件事情是,樱桃在树上是次第成熟的,一个大棚从摘第一颗樱桃到摘最后一颗樱桃,大概要两周的时间。
每年三月,樱桃结果但还没熟的时候,樱桃贩子就挨个棚子跑,和果农谈判。谈妥后就交两万块订金,约好四月樱桃贩子带工人来摘樱桃,不管大小好坏,只要樱桃出棚,都按20块/斤算钱。这种预订樱桃的方式,叫包棚。
但是,每年,樱桃的市场价格波动都很大。万一樱桃摘下来,樱桃贩子发现他只能以16块/斤的价格出清,他岂不是越摘越亏吗?所以遇到年份不好的时候,樱桃贩子的策略是2万块订金不要,电话关机,人就蒸发了。果农天天手搭凉棚,在樱桃树下望穿秋水。没两天,樱桃全烂了。
可是,如果是年份好呢?比如樱桃贩子甲,三月和果农张三谈好20块/斤的包棚价格,到了四月,樱桃贩子乙跑来找张三,说你这棚樱桃我30块/斤全要了。这么一来,张三就会找各种理由,与樱桃贩子甲毁约。
我听到过最欢乐的毁约理由是:张三说樱桃贩子甲拉樱桃的小皮卡自重太大,把他垫路的铁板压弯了。张三说:“别人的车走都没事儿,就你的车有事儿。你这车有猫腻,虽然我还没想出来有什么猫腻,但你这人肯定不地道,我不和你做生意了”。啪!2万块甩在樱桃贩子甲脸上,扭头把樱桃卖给乙了。
我一个种樱桃的朋友就来咨询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果农和樱桃贩子双方遵守包棚协议呢?很惭愧,我当时没想出办法来。因为樱桃贩子流动性极高,年景好的时候,果农张三一咬牙遵守了包棚协议。第二年年景不好,樱桃贩子却不见了,你让张三情何以堪?
李森的这本书,给我提供了完美的答案。
他的第三章,讲的就是一个和大连樱桃非常类似的故事。说的是19世纪的时候,安哥拉分两种人,一种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讲葡萄牙语,能和白人沟通;另一种是住在内地的人,他们猎取象牙、采集蜂蜡和橡胶。
住在海边的人组成商队,用从白人那里得到的烟草、杜松子酒和玻璃珠子,去内地换象牙等东西。与内地一个个孤零零的部落相比,商队人多,机动性强,更重要的是,手上有枪。
所以,如果部落生产的东西太少,商队就不愿意长途跋涉来一趟,那么部落里的人就失去了抽烟喝酒用玻璃珠子打扮自己的机会。可是东西太多了呢?商队又会见财起意,直接动手抢。别说抽烟喝酒了,命都搭进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部落生产者的策略一是索要贡品,没有贡品就没有交易,以增加商队的沉没成本。第二个策略是以赊账的形式要求先得到烟草和杜松子酒,从而把现货交易转化成了订单生产。商队可以抢走现货,却无法抢夺未来才能兑现的订单。
那么,商队怕不怕部落民酒喝光、烟抽完,到交货的时候往地上一躺,要杀要剐您随意呢?商队不怕。因为,交不上货的话,他们会真杀人放火,而不是随便说说,部落民是害怕的。更重要的是,虽然官方已经禁止了奴隶买卖,但是非法的奴隶市场还在。如果部落民交不上货,商队可以抓几个人卖掉,自己的投资是有保障的。
赊账,看似是一个很小的改变,却相当于引进了信贷机制。也就是说,通过改变成本-收益结构,部落民引导商队放弃硬抢,转而与自己做交易。
更妙的是,如果某商队与某部落之间达成了这种赊账信贷机制,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商队就不允许别的商队欺负自己的合作伙伴。借助商队与商队之间的制约,没有枪、又动不了的部落,普遍得到了安全。
类似这种敌对群体之间秩序的建立,还有很多例子。
比如一战期间英德两军长期陷入堑壕战,大家都苦不堪言。渐渐的,双方产生了默契,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开枪、晾衣服的时候不开枪、节假日不开枪、对卫生兵不开枪,等等。双方士兵都严格遵守这些不成文的规定,甚至上级军官都无法强迫己方士兵违反这个与敌方达成的契约。
第二个例子:英格兰-苏格兰《边境法则》
安哥拉的商队与部落民之间、英德两军在堑壕里的士兵之间,敌对的双方可以建立起一定的秩序,以实现双方互利。但这种秩序都比较简单。
那么,敌对的双方,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比较高级和复杂的秩序,比如一个法庭呢?答案是肯定的。李森在书中,举的例子是英格兰-苏格兰的《边境法则》。
从13世纪一直到16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两边的居民都热衷于跑到另一边去杀人越货,当然主要还是抢牛羊。因为犯罪行为都是在另一边发生的,本国法律也就管不着了。
这么抢来抢去的,积怨越来越深,生活生产大受影响。于是双方组建了完全发自民间的法庭,就是各出一名德高望重的绅士,然后由这两名绅士各自从对方那里挑选六名陪审员,组建法庭,在休战日对等受理双方的诉讼。英格兰六名陪审员审苏格兰原告的案子,苏格兰六名陪审员审英格兰原告的案子。这样一来,如果一方判案不公,立即就会遭到对方的报复。
判决公正还好说,并不算难。但是要让来自对方陪审员的判决在自己这边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就显水平了。
英格兰和苏格兰两边边民的办法是,判决下来后,比如判苏格兰的张三赔偿英格兰的李四100块钱。那就得给张三时间去筹钱。那么,张三首先就是要派个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去对方当人质,钱凑够了才能把人赎回来。
那要是张三在家里挑个饭量大的,在李四家住在李四家吃,到约定的时间根本不来赎人,怎么办呢?那到了下一个休战日,李四就可以拿剑挑着张三的名字,公然辱骂。
要是张三就是脸皮厚,脑袋一缩死不吭声呢?到了这个程度,苏格兰那位德高望重的绅士就有责任公开宣布张三为“不受保护的人”。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抢张三家东西,而不会受到惩罚。
在这种机制之下,可想而知,很少有人胆敢不服从法庭的判决,虽然这个法庭完全是来自民间的一个草台班子。
没有惩罚就没有秩序
在《秩序》这本书中,李森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就是在政府完全缺位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秩序在短时间内迅速产生。人们并没有像霍布斯预言的那样,陷入到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的丛林状态。
但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发现,自发的秩序,总是离不开对公平的维护,以及对秩序破坏者的惩罚。即使惩罚不来自政府,但是惩罚却必不可少。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张不要法律、不要法官。完全凭借自由、平等和同情心,来消除社会的恶。他的这个念头,还真的被实践过。
1965年,三个刚毕业的美国大学生在科罗拉多买下一小块林地,要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乌托邦部落。反对一切强力、威权和胁迫。一句话,一切全凭自觉。
开张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叫彼得·兔的人,他既不把钱拿出来充公,也不参加劳动,还去镇上偷东西。更过分的是,还从公家账号拿钱去镇上吃牛排。第二年初,彼得·兔不顾所有成员反对,又张罗了一个音乐节。这下好了,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涌来了一大堆瘾君子,嗑药,乱交,把部落搞得一塌糊涂。但是事先说好的,不能有惩罚,不能有任何强迫,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创始人走了,彼得·兔留下来了。
另一个例子,是1963年在华盛顿州成立的托尔斯泰农场。这个农场“拒绝承认一切规范,接受任何形式的思想和行为。如果说有什么规则的话,那只有一条,就是不能赶任何人走”。这下好了,有一言不合就把别人房子烧了的,还有朝别人房子开枪的……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没有政府,秩序仍然可以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惩罚,则任何秩序都不可能维持运转。所以克鲁泡特金们的主张是不靠谱的。
好!今天,我们介绍了彼得·李森的第一个冒似激进的核心观点,就是在甚至彼此敌对的群体之间,也仍然可以产生自下而上的秩序。更极端的情况是海盗、黑社会这些不法之徒群体,根据李森的研究,他们内部也会产生秩序。
明天,我们介绍他的第二个激进的观点——即使范围扩大到一个国家那么大,自下而上的秩序也仍然会被建立起来。他的这个观点,站得住吗?好,我是顾衡。咱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