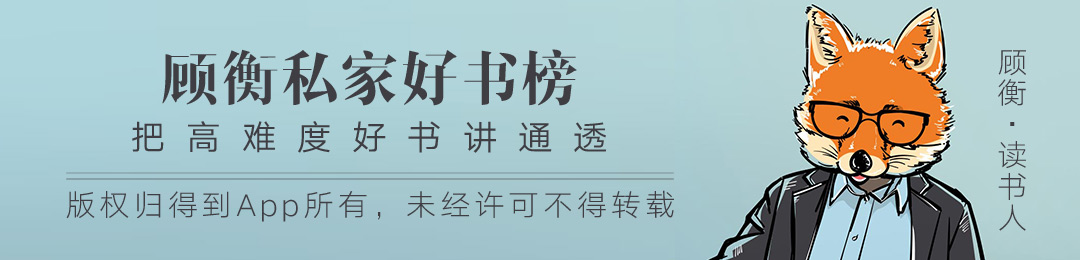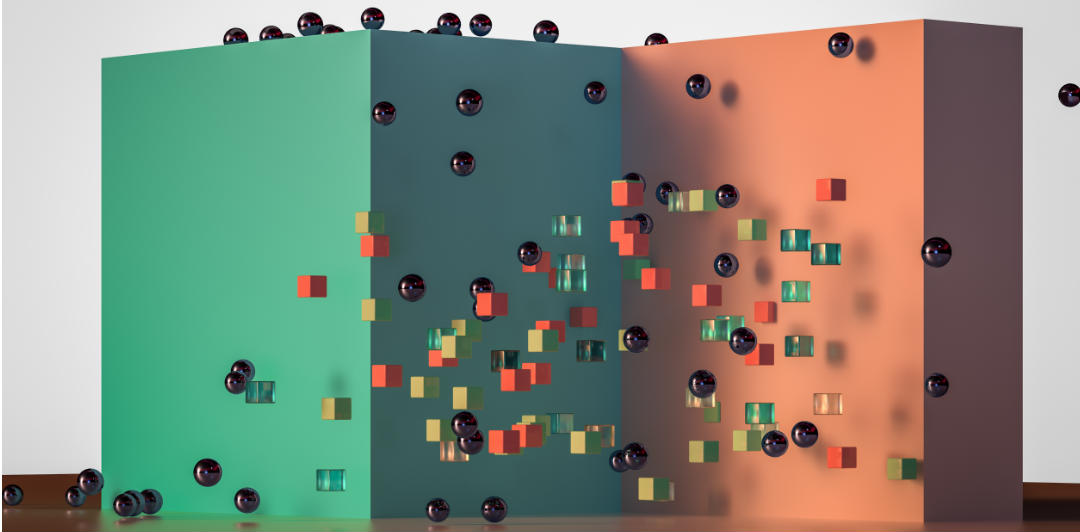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本周我给你带来的是彼得·李森的《秩序—不法之徒为何比我们想象的更有秩序》。
说到秩序,一直就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线之争。自上而下的,就是主张政府管一切;自下而上呢,就是主张政府克制,为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留出空间。
那么,这两条路线是怎么来的呢?它们的差别又在哪里呢?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秩序靠什么维护?
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要有政府?这东西是怎么来的?政府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我们把政府出现之前的社会,叫自然社会;把政府出现之后的社会,叫政治社会。
那么,什么是自然社会呢?庄子描述的赫胥氏的样子,就是“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意思是呆着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走着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嘴里叼着牛肉干,嘻嘻哈哈,一天到晚开心得不得了。这个,就是自然社会。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说可拉倒吧,自然社会哪有这么美好。吃的根本就不够。还鼓腹而游呢,肯定是为了半拉馒头,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霍布斯认为,为了终止大家抢来抢去的状态,也就是“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的丛林社会,就必须得有个说了算的,大家都得听它的。霍布斯管这个说了算的东西,叫利维坦。利维坦这名字来自于《圣经》里的一种怪兽,样子很像鳄鱼,我们就当它是个鳄鱼怪吧。
霍布斯认为,只有在利维坦的强制管理下,社会才会有秩序,自然社会才会进化到政治社会。今天,这个鳄鱼怪又有了另外一个更被人熟知的名字,叫政府。
詹姆斯·麦迪逊虽然自己当了美国第四任总统,但是他把政府视为最大的耻辱,因为它彰显了人类这个物种“卑劣的品性”——必须得有个东西管着,不然就一切人和一切人天天打。
说实话,正是麦迪逊这句沉痛的抱怨,让我对霍布斯的理论产生了怀疑。因为小到蚂蚁,大到狮子,大自然中所有的群居性动物,都没有陷入一切蚂蚁与一切蚂蚁、一切狮子与一切狮子开战的状态。说只有我们人类这一个物种必须得有个外力管着,不然就会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了,这个不合常理。况且,如果我们人类之前是这么个活法的话,恐怕也早就灭绝了。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也不同意霍布斯。洛克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给了我们道德,也给了我们关于公平的概念,不至于就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了。
上帝在我们心里放置了公平的概念,这个想法似乎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其中的一个实验是这样的:比方说妈妈给大林100块钱,让他制定一个分配方案,和弟弟小林分。如果小林拒绝了大林的分配方案,这100块钱就由妈妈收回。
那么,依据经济理性人假设,大林就是给小林1块钱,小林也应该接受,因为1块钱总好过没有。但是实验证明,如果大林给得太少的话,小林宁可自己一分钱不得,也会拒绝,让大林也一分钱得不到。
这个实验在各文化、各人种之间都做过。结果是,咱们东亚人最讲究公平。东亚的大林,平均出价达到38块,是所有人种中给得最多的。
那你可能会说,大林给小林分38块,并不是出于公平,而只是怕小林报复。也就是说,结论可能并不是东亚人更慷慨、更公平,而是东亚人更小心眼儿,报复心更强。
实验者也想到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他们又请了妹妹小娟来暗中旁观。规则是:给小娟20块钱。如果她认为大林不公平,她可以交给妈妈钱,让妈妈惩罚大林。只要小娟给妈妈1块钱,妈妈就没收大林3块钱。给2块没收6块,依此类推……
那按照经济理性人假设,小娟拿到这20块,一溜烟就买冰激凌去了。大林小林公平不公平的,管我屁事儿。对吧?但是实验结果证明,不是这样的。小娟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交钱给妈妈,去惩罚大林。
嗯,这就是洛克的想法。他认为人们心中有先验的、天生的,关于公平的概念。这阻止了一切人与一切人开战状态的发生。
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权限的大小:
霍布斯认为,因为一个人垄断暴力比所有人都使用暴力好,所以暴力的垄断为暴力本身提供了合法性。谁来垄断暴力呢?政府。这样对大家都好。
而洛克的想法是,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只有到了商品经济时期,尤其是货币被发明之后,人们开始种更多的粮食,吃不了拿去卖,于是产生马太效应,强者良田万顷,弱者无立锥之地。这导致了土地的稀缺,矛盾激化。这时候,上帝就不大管用了。
虽然两个人有挺大分歧,但是在基本立场上,两个人却是一致的。就是,霍布斯和洛克都认为,不管喜欢不喜欢,政府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好。
没有约束能产生秩序吗?
当然,也有彻底反对政府的。认为这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出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他的主张是“不再要法律!不再要法官!唯有自由、平等和人类实际上所具有的同情心,才是有效的屏障,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某些人的反社会本能。”
克鲁泡特金反政府,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就像前面我提到过的,大自然中其他群居性动物都好好的,凭啥只有人类需要个政府?第二个,以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制,总是对道德的一种羞辱。一个人遵守法律,不应该是出于对惩罚的恐惧,而只是因为遵守法律规定符合他的道德准则。只有这样的生活,才称得上是有尊严的生活。
但是,说某些人反社会,其实就是坏人呗!比如村里有个二赖子,怕辛苦不肯劳动,邻居一出门种地,他就跑到人家去偷粮食。对于这种人,克鲁泡特金所说的“自由、平等和同情心”,是不是有效的屏障呢?万一这屏障不顶事儿,又该当如何呢?
无政府主义者说“大自然没有小偷,是先有政府后有小偷的”。那有人就说了,咱不管是先有小偷还是先有政府吧。好比现在有筐苹果,里面有烂的了。不拿出来就会传染好苹果。咱们要不要把这个烂苹果拿出来?怎么拿?
讲道理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会同意烂苹果必须要被拿出来的。如此一来,不还是强制吗?那你无政府主义者说你遵守法律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自愿,这个说法不就是扯淡了吗?
到这里,真正的分歧才暴露出来。就是,克鲁泡特金说的遵守法律必须是出于道德上的自愿,这是个假问题,并不能成立。真正的问题是,大家都同意要对坏人进行惩罚,不然整筐苹果就烂光了。但是,这个惩罚是否一定要来自政府呢?
1968年,美国的一个生态学教授加勒特·哈丁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个命题。他说,如果一块草场由张三和李四两个牧羊人共用的话,他俩一定会拼命多养羊,过多的羊迅速把草吃光,所有的羊就都饿死了,然后张三和李四也饿死了。
哈丁主张,为了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政府必须介入,派官员来,限定张三和李四羊群的数量,不然这两个蠢货一定会周而复始地陷入公地悲剧。那制度经济学家们就不同意,说干嘛一定要政府出面呀?拦道铁丝网,把草场一分为二,不就完了吗?谁爱养多少羊就养多少。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们用明晰产权的办法,来代替政府的行政干预。
可是,在大草原上拦铁丝网,这个很费钱。更极端的情况是,你说草原拿铁丝网拦起来,这个可以有。可是如果是一个渔村的渔民,共用一个渔场,这个怎么办?海上乍拦铁丝网呢?
自发秩序有可能吗?
好!关于秩序如何建立,有两派主张。一派是哈丁,接受霍布斯的思想,认为必须政府出头,不然就乱套了。另一派是制度经济学家,接受洛克的思想,认为争端可以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政府起什么作用呢?政府就做好一件事:保护产权。
但是,有些东西的产权确实就没法明晰。比如一片渔场,怎么分到户呢?对于不可分的公共资源如何进行有效处置,研究这个问题最深入的,就是艾莉诺·奥斯特罗姆。她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可惜死得太早。
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对大量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土耳其一个小渔村的例子,就很经典。这个村子里的渔民,是如何公平地分享全村唯一的一片渔场呢?村民们的办法是用浮标把渔场分成大致的几十块,每个渔民一块。然后,每天按顺时针方向,每个人挪动到邻居家的那块,这样每块区域不论质量好坏,都是大家轮着来。
这个办法,已经运作好多年了,从没发生过有人耍赖的事情。每年捕鱼季节开始的第一天,渔民们聚集在小酒馆里,一起喝上一杯,重申一下规则。这一天,渔民们也会请当地的一个警察出席,作为见证。不用合同,不用签字画押。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办法当然非常好。又省了律师费,又不伤和气。但是,如果几个不同的群体,彼此还有矛盾。他们之间,能自发产生秩序吗?又或者,范围扩大,一直扩大到一个国家那么大,自下而上的秩序,还能建立起来吗?
李森的这本书,回答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好,我是顾衡。明天,我们开始介绍《秩序》这本书。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