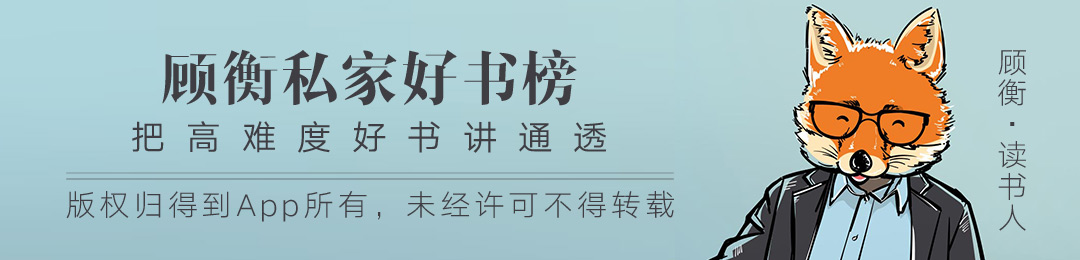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前两期咱们讲了,汉朝皇帝们用给百姓赐爵和削藩这两个办法,以实现从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型。除了这两件事,他们还干了啥别的呢?今天再来讲第三件:打豪族。
皇帝与豪族的“竞争”
刘邦刚建国,他的手下娄敬就跟他提建议,说你看咱们当年打秦国的时候,别看起头的是陈胜吴广,但是闹腾了没多久,他们自己内部就乱了。吴广是和自己人吵架被杀。陈胜更窝囊,是被自己的车夫刺死的。泥腿子,起不了什么大浪。心腹大患,还是以前老六国的那帮贵族大户,就是项羽那样的。所以啊,咱应该把这些豪族,都弄到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而且他们还有钱,可以拉动首都消费。首都的老百姓有生意做,有钱赚,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不会搞事情了。
刘邦深以为然,就下令全国的豪族,就是齐国的田氏啊,楚国昭氏啊、屈氏啊(屈氏就是屈原他们家族),拖家带口的,都给我搬首都来。
来了之后,刘邦还给他们赐了新的姓,让他们尽快忘本,尽快拆成多个小家族。比如齐国的田氏,是个非常大的家族,人非常多。刘邦按先来后到,第一拨来的,赐姓第一;第二拨来的,赐姓第二。老田家打掉牙往肚子里咽,除了谢主隆恩,也不敢说啥。
不用老百姓出手,皇上直接就把土豪给撵走了。那这些大户人家都迁走之后,村里只剩下平民百姓,家家分100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又赶上了好皇上,收税特别少。汉朝只有高祖刘邦的时候田租有1/15,后面都降到了1/30。遇到灾年还减免,借给农民的种子,皇上一高兴就说不用还了。在汉文帝期间,甚至把田租全免掉了,时间长达12年。
那么,汉朝的老百姓,是不是就过上好日子了呢?并没有!那你说皇上都不收租子了,这老百姓咋还过不上好日子呢?
咱们又得从周朝开始捋这个事情。西嶋定生提了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对。他说,春秋的时候,贵族统治者是氏族结构,平头老百姓也是氏族结构。到战国时期,氏族结构就垮掉了。
原因有两个,一是贵族要平民当兵打仗,那么就要齐民编户,把氏族拆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
二是铁制农具开始普及。以前没有铁犁,开荒需要全氏族老少爷们一起上。现在有了铁犁。我媳妇在后面扶着,我在前面代替大牲口拉着。这么辛辛苦苦整出来的五亩地,凭啥打出来的粮食要归整个氏族呢?所以,自留地就出来了。
自留地一出来,大家都有了私心,氏族也就垮掉了。这说的是平民、被统治阶层的氏族结构,在战国时期逐渐向一夫一妻小家庭转型。
那贵族统治阶层呢?也同样存在这个倾向。在氏族社会的时候,别说财产了,连女人都是共享的。老爹死了,他的小老婆归儿子,这个叫蒸;兄弟和叔叔死了,嫂子和婶子归弟弟或侄子,这个叫报;还没死呢就共享上了的也有,这个叫通室之好。总之,都不是外人,各种乱。
那么,老打仗老打仗,就有好多打了败仗的贵族,自己的氏族没有了,主子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去投奔别的贵族,去人家家里当门客。咱们读《战国策》,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的,门下食客三千。这些食客,就是日本浪人一样的,失去了自己宗族的战败贵族。
那么,春申君孟尝君,他们养这么多门客干嘛呢?就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再组织。
比如有一大块地,要是能有灌溉条件就好了。这个事情农民自己干不了,他们缺钱,也缺组织能力。这时候,春申君就出面张罗,组织老百姓修建水利工程。然后,再把这些新开垦出来的耕地租给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春申君就需要管理人员。他的门客,就是干这个的。
你看,春申君和一个房地产开发老板没啥区别。他也是去弄块地(当时地有的是,也不用招拍挂),再划拉些包工头,也就是门客,让他们雇些民工来,修路修渠,清理灌木,开垦出很多荒地。
然后也和卖房子一样,到处吆喝:乡亲们快来租我的地啊,小茅屋都给你们建好啦,拎包入住啦!我这儿还有物业配套,谁家缺个牛缺个锄头,还能到我这儿来借……人来了,地种上了,他也就收到租子了。
西嶋定生说,春秋末年,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氏族的解体,是同步发生,并且互相促进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他说,秦汉时期的一夫一妻农民小家庭,绝不是自然发生的,这后面是有推手的。这个推手,就是贵族。因为,虽然贵族和平民旧有的秩序,也就是氏族,都在崩溃,但是平民却并没有重建新秩序的组织能力。
于是,就像前面说的,出现了春申君、孟尝君这样的人物,他们把失败的贵族收纳为门客,形成了新的管理层,继而完成了对平民的再组织工作。而秦的商鞅变法,不过是把这个工作提升到国家层面,让国家变得强大起来。
而信陵、春申、孟尝和平原这君那君的,却是在挖自己国家的墙脚。因为他们的改革成果,并没有贡献给国家,反而加速了平民逃离国王的过程。这一步改革没跟上,秦与六国的胜负,也就被决定了。
你可能有个疑问,春申君、孟尝君这些人,你们说开发块土地就开发啦?土地不是国王的吗?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啊,春秋时候,一国之内的统治单元是城,城与城之间有很多空白的“非国家空间”。春申君、孟尝君就在这些空地上开垦新土地,吸引本来给国王交租子的农民来给他种地,你说他是不是挖墙脚啊?
那说这些,和汉朝打豪族有什么关系呢?
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豪族和国家是一种竞争的关系。竞争什么呢?就是争当农民的组织者。如果是国家当组织者,那就像秦国一样,越来越强大;如果像老六国那样,任由豪族去挖墙脚,国家就弱了。
汉朝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比如贾谊和晁错,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认为把社会上所有的豪族,上到春申孟尝这个级别,下到在一乡一村里只有几十个佃户的地主,全部干掉。这样,挖国家墙脚的春申孟尝没有了,项羽这种能造反的强人也就被扼杀在萌芽当中。他们的这个想法,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当然也会受到皇帝的支持。
清除豪族的结果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今天咱们已经有了普遍的共识,就是社会像个生态圈,必须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能支持各种各样的交易情境,让所有人在高频次的服务与产品交换中致富。
但汉朝的皇帝和知识精英并没有这样的见识。他们更没有詹姆斯·斯科特那样的见解,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对社会进行简单化和均质化改造的过程,一定会伤害到社会,最终导致动乱。
从汉高祖刘邦把老六国的顶级豪族迁到关中之后,这就成了汉朝的一项基本国策。再到后来,地方官员的家属,也被迁到这些新城。一是你老婆孩子在我手里,当个人质;二是你当完官也别回家祸害乡里了,我已经把你老婆孩子安置在首都了。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么个搞法,把基层的士绅组织者全部拔掉,出现了严重的后果。
因为,农民种地,不仅要交田租,还得以现金的形式向国家交别的税,具体说来,就是算赋,也就是人头税,15-56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一算,一算就是120个铜钱;3-14岁的小孩子,一年也要交20个铜钱,这个叫口赋。除了这两项人头税,还有訾算,就是财产税,税率是一万钱交一算,就是1.2%呗。
这么总的算下来,凭良心说,税并不重。但是,农业这东西,靠天吃饭,收入极不稳定。
今年发大水,如果你是地主家的佃户,因为彼此知根知底,所以会有商量。今年不行了,欠着,明年再还;但是现在地主都被押到首都去了,你现在是自耕农,遇到荒年,你就只能向商人借贷,约好明年再还。可是,明年又赶上闹蝗虫,这债还不上呢?地就没了。
地没了,你就得给商人当佃户,商人收多少租子呢?50%。你看,朝廷只收3.3%,现在你一个资金周转不开,变成了商人的佃户,田租就变成了50%。差距就是这么大。交了一半的收成,人头税和财产税拿啥交呢?所以这日子就没法过。
那你可能要问了,给贵族和地主当佃户也是佃户,给商人当佃户也是佃户,有啥不一样的呢?非常不一样!贵族也好,地主也好,他们有对土地的忠诚。因为他们离不开土地,所以他们就懂得与佃户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且他们互相知根知底。
而商人,虽然发了财买地当地主,但他与土生土长的贵族和地主不一样的是,他没有那份对土地的忠诚。他追求的是货币,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更多的本金、更高的流转速度。农民丰收也好,破产也好,商人的诉求都是在现有条件下立即得到最多的回报。
那皇帝就会这么想:哦!我平常只收3.3%的租子,遇到荒年还减租,还开仓放赈。你们这帮奸商却在趁机巧取豪夺。所以也不光是汉朝,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商人恨之入骨,制定政策打压商人,对商人征收重税。
但是,汉朝的皇帝们,和贾谊、晁错这些知识分子想不明白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大力打压了豪族,造成社会基层的组织真空,才让商人乘虚而入的。他们越是对商人征重税,商人就越是要把这个税收转嫁到自己的佃户身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朝廷对农民的减税呢,又造成投资土地更大的利润空间。商人更要买地了!
这可怎么办呢?下一讲,咱们就来聊聊商人的问题。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陪伴和收听,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