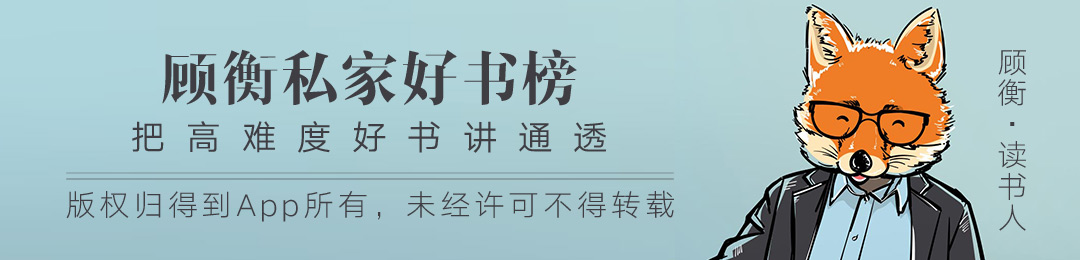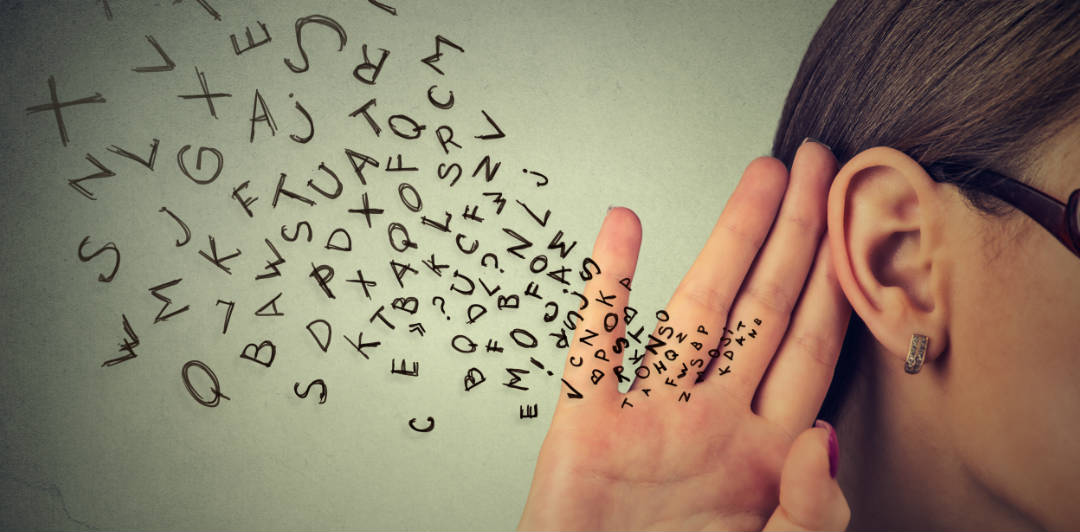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这一期,我们继续介绍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就是《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
上一期咱们请出了波兹曼的老师麦克卢汉,也介绍了他的核心观点,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信息的意思是说,媒介不仅决定了信息的样式,更决定了信息的内容。对于老师麦克卢汉的这个观点,弟子波兹曼是接受的。师徒二人的学说,被称为媒介环境说。
师徒二人的共识和分歧
那么,麦克卢汉和波兹曼是不是在主张一种技术决定论呢?就是说,媒介是决定性的力量,信息对媒介只是被动的适应。不是!
既然“媒介即信息”并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那麦克卢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麦克卢汉用了两个大词来做了解释。第一个大词是“主动完成”。“主动完成”的意思是,工具是欲望的延伸。比如后背痒痒,够不着。这时候人们就想,要是手臂长一点就好了。这个欲望,产生了痒痒挠这个工具。
第二个大词叫“结构冲击”。是说工具被发明和使用之后,也会改变人们的认知结构。比如,你手上有个锤子,那你看到什么都想去敲一敲。要是你手上有个扳手呢?那你看到什么都想去拧一拧。
麦克卢汉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文化想象成一个生态圈,那么,媒介这个怪兽并不是外来的,而是生态圈内生的,是文化的欲望外延和物化的产物。另外,大怪兽长出来之后,它会对生态圈产生影响。对于这个到处敲一敲拧一拧的影响,文化生态圈有顺从,也有抵抗;有适应,也有改造。
所以,麦克卢汉并不认为技术是外在于文化的,更不认为技术能够决定文化。
“媒介即信息”,更准确的解读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同样一个信息,你是听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还是自己在书本上看来的,还是通过广播知道的,即使信息内容一模一样,但是本质上已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对你这个接收者起到的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波兹曼和麦克卢汉没有分歧。但是在另一个问题上,师徒二人的立场就完全对立了。这个对立,也就是咱们这一期要想的重点,其实也是《技术垄断》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两个人在什么地方有分歧呢?对技术革命是悲观?还是乐观?这个基本态度不一样。也就是说,传播技术的提高,对人类社会是件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老师麦克卢汉认为是件好事儿,信息传播越是高效,就越有利于民智的提升、道德共识的建立、社会的平等和个人的自由。总之,好处一大堆;波兹曼反对这个。
那技术进步总是好事儿呀!波兹曼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也不好呢?这个,咱们必须扯远点儿,从2000多年前的另一对师徒说起。哪一对儿师徒呢?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耳朵派”和“眼睛派”
在古希腊的时候,对于信息传播这件事,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眼睛派,一派是耳朵派。为啥?因为信息有好多好多种样式,比如周幽王的烽火、语言、文字、图像,但是我们接收信息的器官只有两个:耳朵和眼睛。
你可能会说,不就是接收信息吗?有声音就听呗,有文字就看呗,还分什么派?不然,在古希腊的时候,这就已经是一个很严肃的争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吵得一塌糊涂,谁也没能说服谁。
他俩吵什么呢?既然说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咱们拿希腊神话作为例子,来说明一下两个人的分歧:
古希腊的神话,最开始,可不是写成文字的书,它只是在游吟诗人的嘴里唱来唱去的东西。那嘴巴说的东西,就没个准儿了。还记得上一期张三媳妇给张三打电话的例子吧?如果张三媳妇给张三写一条短信,那张三就会买块豆腐回家。但是张三媳妇打电话给张三呢?结果很可能变成了两口子去外面吃饭,吃完饭再看场电影。
希腊神话也存在同样问题,就是在口述时代,内容是不固定的。整个神话就像一大锅杂烩汤,从里面捞出什么,要取决于听的人是谁。比如荷马到了雅典,雅典的大英雄是谁啊?是忒修斯,那荷马就得以忒修斯为主线来编排故事内容;他跑到底比斯呢,底比斯最有名的神话人物是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啊。这么着,神话故事就得重新编排。
也就是说,在口语时代,神话内容的萃取和重新组织,就像一个网站的编辑给内容打标签——给定的主题词不一样,呈现的内容就不一样。
不仅如此,用口语传播的时候,神与神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是不固定的,这就导致了一个事情的前后因果也会有多种说法。苏格拉底认为这很好,一锅汤能变出18种口味,美人之美,各美其美。口语,保证了阐释的多样性。
苏格拉底还正儿八经地给文字列了几条罪状。比如,文字是固化的,死气沉沉的,哪有说故事那么好听。还有,如果什么都拿笔写下来,那人类的记忆力肯定就会退化。还有,文字让语言失控啊。这也是事实。一旦什么念头被写成了文字,就容易被人利用,被人曲解,它就不再属于你了。
苏格拉底这番话其实是有道理的。你想,如果是2000块的买卖,甲方乙方来回两三个邮件,也就解决问题了。但如果是2000万的生意呢?那肯定要见面谈才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于人类来说,口语表达意思更直接,更不容易误会。
但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不同意。
柏拉图说你这不是瞎胡闹么?一件事情,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放之四海而皆准。谁是爹谁是儿子,三舅妈二姑父的,辈分不能乱了!这么着写下来之后呢,神的谱系就成了一个树状,而不再是一大锅杂烩汤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再把神话说出来,而改成写下来之后,神话内容就具有了一种全新的结构性。你看,同样的神话,说和写,不仅样式不一样了,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字,连内容都不一样了。这也是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师徒俩是不是当面争论过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苏格拉底一辈子没有文章和书留下来。而柏拉图写了好多东西留下来。所以你看,苏格拉底是不是耳朵派?柏拉图是不是眼睛派?
文字与口语的差别
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文字,但是文字是有很多好处的。归纳一下,大概有这么三个吧:
首先,文字可以长久保存,这使得知识的增量成为可能。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知识传承仅限于供养一个岁数最大的老奶奶,效果和咱建个图书馆差太远了。
其次,文字打破了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同时在场的限制。比方说有个饭店,从老板到伙计,没一个识字的,那就很麻烦。老板派伙计张三去集上买鸡蛋,张三前脚走,老板发现酱油没有了,大蒜和白糖也得再买点儿,另外还得添20双筷子和8个盘子,派李四去追。好容易追上了,气喘吁吁地一摸脑袋,啊呀,老板让我跟你说还要买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你说这情可以堪!
最后,文字最重要的,是相比于口语,文字有发明概念的自发冲动。“物质”、“本体”、“逻辑”、“伦理”这些抽象的大词,没法在自然界用手指出来,也就很难在口语环境中产生。我们人类是因为使用了文字,才产生了复杂而精妙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不是因为有了复杂的逻辑思维能力,才发明了文字。
你看,文字作为一个媒介,又一次证明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就是,我们想把信息写下来,别忘了,这个主观欲望,催生了文字,这个是麦克卢汉所说的“主动完成”;而文字的使用呢,又使得人的大脑更加擅长抽象思维,这就是“结构冲击”。
前面说了,用文字把希腊神话写下来,会产生固定的人物关系,以及事件清晰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话,整个神话就具有了树一样的结构性,而不再是一大锅杂烩汤了。文字的使用,不仅会让信息产生结构性,同时,也会让政治产生结构性。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相比于口语,文字很复杂,需要大量的学习时间。一件不太复杂的事情,三岁的孩子就能说清楚。但是要写下来,并且文通字顺,至少要到十五岁。这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掌握文字的门槛是如此之高,即使人人会阅读,也不等于人人会写作。
这样,就产生了知识精英阶层。少数人写,多数人看。有编辑作为把关人,决定大众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这是文字传播的特点。福柯说:“知识分子依靠对知识进行定义和分类,掌握了对这个世界的霸权。”意思是说,文字的生产和传播,与政治权力的生产与分配,实现了完全的同构。谁控制了文字,谁就拥有了权力。文字天然就是反民主的、集权的、精英的。
从1450年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到今天,五百多年就这么过去了。眼睛派,也就是文字文化,本来已经彻底赢了。但是这个时候,广播和电视来了。局面发生了翻盘。上世纪30年代,广播在西方普及了。上世纪60年代,电视在西方也普及了。
听广播看电视没有门槛,不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小孩子甚至在学会说话前就喜欢看动画片了。麦克卢汉敏锐而深刻地宣称:“听觉回归了”。意思是文字的高门槛被取消了。风水轮流转,苏格拉底又回来了!
你看,有意思吧?两位老师,苏格拉底和麦克卢汉,都是耳朵派的,他们热情拥抱信息民主化的过程。而两个徒弟,柏拉图和波兹曼,却是眼睛派的,对信息的民主化进程深恶痛绝。
那波兹曼为什么对信息的民主化如此深恶痛绝呢?下一期,咱们就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