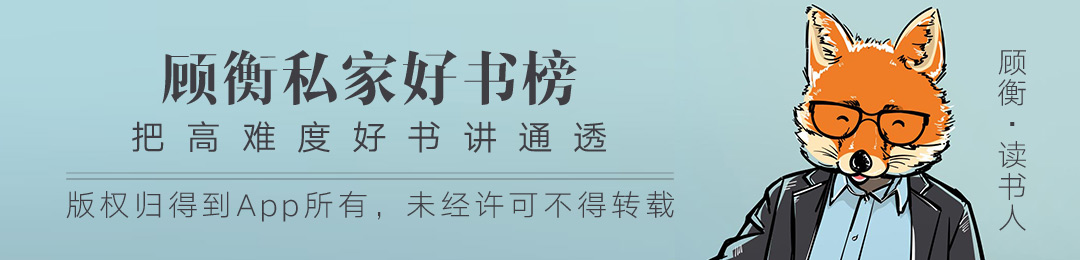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这一期咱们继续介绍斯特科的《国家的视角》。
昨天咱们说了,古代的国王有两个强烈的愿望,一个是让他的老百姓都一堆儿一堆儿的住在一起,别跑来跑去的,方便他收税;二是他希望能越过中间的贵族,掌握老百姓的信息,以便实现直接统治。
这个问题,咱们也并不陌生。多年前,黄仁宇就写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与财政》,分析了中国无法实现数字化管理的原因,痛心疾首的。斯科特这本书的意思等于是在说:黄先生您别难过了。不光是你们中国古代,我们欧洲也一样。而且,前现代的欧洲真的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之后,反而更糟、更可怕。
数字化管理是好事情呀!为什么斯科特认为西方前现代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反而更糟糕了呢?
斯科特说,所谓数字化管理,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次重构。人口、各种事物一定要被重新分类定义。除非经过巨大的抽象和简化,否则就没有办法描述任何现实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必须忽略大量的非结构性数据,你才能做出一张excel表格。
这个表格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斯科特总结了这么五条:
- 它们只搜集了国家感兴趣的事实(征兵、征税、政治控制)
- 它们是成文的,或者数字的
- 它们是静态的
- 它们是被格式化的
- 它们将个体进行了分类
“科学管理森林”为什么失败
斯科特举的第一个例子,是18世纪普鲁士王国的森林。
现实的森林很复杂,各种树都有,乔木下面还有灌木、草、花、地衣、苔藓,与各种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一起,为森林提供了动态的、多元的生态环境。周围的居民也可以去森林中捡柴禾和采蘑菇。
但是,普鲁士国王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只有一个:我的这片森林,每年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
那么对于国王任命的林业官员来说,森林所有其他的参数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参数:每年能为国王提供多少立方米的木材。就这样,复杂的、现实的森林被处理成了简单的、抽象的森林。
也就是说,这里不仅仅是个能力问题,更是个目标导向的问题。鸟类还有没有合适的树做窝,周围居民还能不能采到蘑菇,国王的林业官员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这是科学林业的前提和基础。
于是,所谓的科学林业,首先就是清除灌木,便于日后的伐木作业;其次,伐一棵,就补种一棵挪威云杉,因为挪威云杉材质坚硬,价格高,生长速度还快。最后,补种的时候,要按规划种成排,树间距不是由树木的特性来决定,而是由伐木机械所需要的作业半径来决定的。
这么着,原生林被伐了一遍之后,普鲁士的森林全部被替换成挪威云杉,整整齐齐的,像士兵列队。灌木被定期清理,倒下的枯树也会及时拉走。整个森林里干干净净的。普鲁士的林业官员还用各种办法来测量不同树龄的树的体积,从而可以预测每年木材的产量,定期向国王报告。
总之,普鲁士国王的森林,和别的国王的森林不一样。普鲁士国王可以清晰地知道,他的森林里有多少棵明年就能砍伐的云杉,能生产出多少立方米的木材,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让其他国家都羡慕不已,觉得这样的“科学”真好,纷纷效仿。
因为树木的生长周期很长,等到危害被发现之后,大错已经铸成。
单一树种的次生林,导致树种退化、土壤贫瘠、病虫害失控……即使不考虑消失的动植物,和捡不到蘑菇的周边居民,单说国王的木材收入,也急剧下降了。不论是生态环境、经济效益、社会效应和审美价值,从任何一个维度来衡量,德国所谓的“科学林业”都是一场灾难。
科学管理森林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普鲁士国王们继续简化经济、简化社会的冲动。
原因很简单:对于国王来说,一个复杂得无法统治的社会,对他不仅是无用的,甚至还是危险的。所以,即使简化会伤害社会,那又怎么样呢?对于国王来说,可以控制、可以实施有效统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斯特科这本书的书名——《国家的视角》——就是这个意思。
数字化管理的方式与结果
为了追求简单化、清晰化的目标,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强推均质化。也就是咱们中国人熟悉的“书同文、车同轨、话同音”。所有地方上的特殊性,在古代皇帝看来都是讨厌的东西。如果全国所有的县,面积也一样,形状也一样,人口也一样,甚至县城的布局也都一样,那该多好呢!这,是历朝历代皇帝的想法。
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就真提过这样的主张,就是用正方形划块块,让每个县形状都一样,大小都一样。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里,每一个城市也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好处是”,托马斯·莫尔说,“一个人只要知道一个城市,就了解了所有的城市。除了自然位置不同以外,其他方面全都一样”。
国家简单化、均质化的诉求,与地方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古今中外都一样,都普遍存在。雄霸一方的贵族只要能力允许,总是要保护地方的特殊性。这涉及到他重要的个人利益。什么个人利益呢?斯科特举的例子是度量衡。
在18世纪之前,法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平常做生意,全靠买家卖家身体的数据。比如卖绳子,就是卖家把绳子在虎口和胳膊肘之间缠绕,绕一圈一毛,绕十圈一块。那人胳膊有长有短呢?这个就不管了,差不多得了。
大斗进、小斗出。咱们中国的地主是这样,法国的贵族也一样。农民对这个恨得不行。盼望国家能出台一个标准的度量衡,免得受贵族欺负。
但是即便有个标准的度量衡,比如在石头上挖个洞,容积等于一蒲式耳,再把这块石头搬到教堂门口,以示“上帝见证的公平”,也还是不解决问题,贵族还是有很多办法来欺负农民。
比如他借给农民小麦的时候,从腰部往石洞里倒,这样就比较虚,小麦之间的空隙就大。到了农民还的时候呢,他要求把麦子举到肩膀上往里面倒。另外,小麦倒满了之后要把表面弄平。怎么弄平呢?借出去的时候,贵族用一把尺把表面刮平。让农民还的时候,他改用小碾子压平了。这一虚一实,可就差得不老少。
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对于古代的皇帝和国王来说,他有强烈的愿望对臣民实施直接统治。
拿周天子来说,实施直接统治的王畿,得到的是真金白银;实施间接统治的封建制,只能得到礼仪性的朝贡,比如用来过滤酒渣的包茅。区别大了去了。
那么为了达到直接统治的目的,国家就要通过人口普查、颁布标准度量衡、制作地图、制定统一的法律,等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王国的简单化、清晰化和均质化。
这个过程,对复杂、多元和有机的社会,总是一种伤害,也是对掌握地方的贵族权力的剥夺。所以,国王的这个努力总是遇到来自地方贵族的抵抗,从而缓解了国家对社会的伤害。
但是中国和欧洲又不一样。中国从秦朝就建立起了中央集权政体,取消了地方自治,由官僚体系对全国进行统一管理。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政治上的早熟。这个早熟的政治体制,与欧洲封建制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进入20世纪之后,国王没有了,全球纷纷建立起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这时候,国家的视角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好!我是顾衡,明天下一期接着聊。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下一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