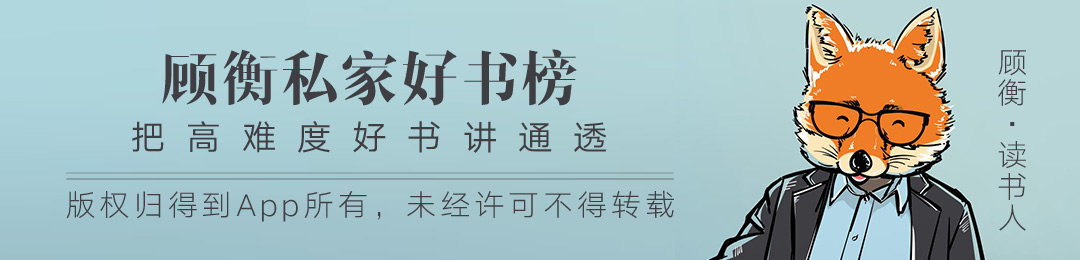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上一期,咱们聊了伯林的思想的基本特点、伯林对阿伦特以及对宗教的看法,也聊到了伯林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正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方法论的厌恶,导致伯林早在1932年就放弃了专业的哲学研究,而转向了思想观念史研究。
在伯林的思想观念史研究中,自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他提出著名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之前,他对于自由的思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咱们还是一边说伯林的经历,一边讲他的思想发展。
伯林的思想轨迹
二战爆发之前,伯林在全灵学院过得挺开心的。因为是第一个被全灵学院录取的犹太人,上流社会的门就算是向他打开了。他不仅是犹太大富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上宾,甚至还成了伦敦贵妇们的社交新宠。丘吉尔的侄女,就是后来嫁给英国首相艾登的那个,对此痛心疾首。她觉得,伯林这种不世出的天才,应该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成为一个圣人,现在可好了,像个知识小丑,在贵妇的饭局里耍些从嘴里喷火的把戏。
这段时间,伯林写了一本《卡尔·马克思》。这本书写得并不好。因为他不懂经济学,所以对《资本论》就没评在点儿上。
伯林不太喜欢马克思,但是马克思有两个地方给了他启发。一是马克思认为思想和观念都具有历史性,也就是,不同时期里,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马克思认为阶级矛盾无法调和。
伯林扩大了这个观点的适用范围。他认为,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和观点分歧,并非只产生于不同的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所以,在二战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伯林坚定了自己反对刺猬的立场。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发现的唯一一条真理,就是不同目标发生冲突的必然性。”
这是个很重要的发现。多年后,美国著名哲学家,《正义论》的作者约翰·罗尔斯就承认,他书里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一个良序社会里,公民可以通过讨论,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共识。在认真考虑了伯林的观点之后,罗尔斯认为自己过于乐观了,他的这个假设并不现实。
因为人是生而不同的。不同的个体,天生就在追求不一致的目标。那么,如果我们把生活交给一只刺猬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想想强盗普罗克鲁斯忒斯的那张床就知道了。所以伯林说:“观念每赢得一次假定的胜利,个人自由就受到一次相应的损失”。
正是认识到这样的悲剧性,伯林当时呼吁说:“时代要求的并不是更强烈的信仰、更有力的领导、更科学的组织,而是一些相反的东西,比如更开明的怀疑主义,以及对差异和道德多元更大的忍耐。”
二战期间,伯林被英国情报机关招募,派驻纽约。任务是通过报纸解读美国的民意和美国政府的政策倾向,就是对美国政府做舆情监控吧。这个工作,对于伯林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写的周报告,连丘吉尔和英国国王都会看。
不仅如此,伯林还利用自己牛津校友和犹太人的身份,迅速与政府官员、报业大亨、专栏作家、工会领袖建立起私人关系,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比如,罗斯福第四任总统任期只干了73天就去世了,杜鲁门接任。英国政府急切地想知道杜鲁门上台后美国政府会有怎样的变化。
伯林在汇报中说:杜鲁门上台后,新总统和国会的关系会改善。美国对战争的投入会加大。而罗斯福,生前虽然被痛恨,但死后却会得到爱戴。他搞的那些新政,也就是总统和联邦政府扩权、福利政策,将永久地改变美国社会,即使是在战后,也会得到延续。
这个预判,可以说是惊人的准确了。可见,“20世纪英国最聪明的人”并不是浪得虚名。
贡斯当的自由论
二战结束后,西方学界因为冷战的关系,又一次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本来已经被人遗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邦杰曼·贡斯当,重新获得了人们的关注。伯林说,关于对自由的理解,贡斯当给了他最大的启发。
贡斯当虽然是个法国人,却是在苏格兰接受的教育,所以他的思维方式更像个英国人,而不像法国人。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休谟,很早就注意到古希腊人与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
现代人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处置财产的自由、宗教自由,这些在古希腊的城邦中都是不存在的。霍布斯就断言,古希腊人说的自由,和现代人说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古希腊人只有城邦的自由,而不存在个人的自由。
- 比如,苏格拉底是因为“不信神和蛊惑青年”而被处死的。说明在雅典,个人并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
- 过节的时候,城邦里的富人会被指定承担哪一项费用,或干脆要求必须捐多少钱。这就好比小区居民投票说,张三家沙发真不错,搬到会所来给大家用吧。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咱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古希腊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 在雅典,不仅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他们还有贝壳放逐法,一个人即使没做错任何事,仅仅因为口才太好、名声太大,就可能被投票放逐十年;
- 另外,开公民大会的时候,雅典的官员会把市场的三面封起来,只留一条通往会场的通道,然后派奴隶拿着蘸着颜料的鞭子,像赶牲口一样把公民赶到会场上去开会。现在,议会里督促议员去投票的角色被称为党鞭,就是出自这个典故。之所以蘸颜料,是因为颜色会留在被抽打的人身上,这是一种羞辱。而在斯巴达,不去开会的人是要被罚款的。
- 除了以上这些,我们还知道,梭伦法典里专门规定了,如果城邦里发生了两派争斗,每个公民必须把自己的铠甲放在自家大门的左边或者右边,以表明立场。打酱油是不行的。
- 也就是说,古代人只有参与公共政治的自由,而且不参加还不行。那在咱们现代人看来,不许不参加的东西这不是自由,而是一种义务或责任。
基于这样的差别,贡斯当把自由区分为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他说,古代人有“做什么的自由”,而现代人,则有“免于什么的自由”。古代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我和奴隶不一样,对于城邦的公共事务,我有权去参与;而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则是我可以免于被强制。
英文有两个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英文有liberty和freedom,在中文中都被翻译成自由,这导致了理解上的困难。当初严复把freedom翻译成自由,而把liberty翻译成自徭。这是个非常美妙的翻译。“自由”,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意义,指一种免于强制的状态。而“自徭”,徭役的徭,服自己的徭役,意思是和同类一起承担一项责任和义务。
德拉克洛瓦画的《自由引导人民》,自由女神光着膀子,喊“同去,同去”,这个是呼朋引类,一起去做某事,是liberty。
而freedom,我不知道你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没有。影片中,安迪反插上办公室的门,用监狱的喇叭播放了一首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外面,狱卒疯狂地砸门;里面,安迪两只手抱着后脑勺,坐在椅子上,脚翘在桌子上,安静地听他的音乐。那一刻,就是freedom。
贡斯当把古代人的自由定义为“做什么的自由”,而把现代人的自由定义为“免于什么的自由”。这个让伯林深受启发。
浪漫主义与自由的对立
但是1950年,伯林第一次接触浪漫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印象很深刻。他认为,正是浪漫主义运动导致了纳粹的兴起,侵犯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把自由按性质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而是引入了浪漫这个概念,作为自由的敌人。
为什么浪漫会成为自由的敌人呢?这就要说到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了。
在卢梭之前,自由这个词,指的就是免于被强制的状态。但是到了卢梭这里,自由却成了只有当人的天性得以实现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的一种东西。自由和个人创造以及个人表达成了同义词。也就是说,自由被等同于人的解放。
那要是有个人说我现在挺好的,我不想被解放。这可怎么办呢?
卢梭说,这个人是被愚昧蒙住了双眼,他不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对这种人要教育、要劝诫。卢梭说的教育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设立审查官,发现有错误的言行,就公开羞辱;第二个办法是设立公民宗教,让大家学会如何正确参与公共政治生活。
那如果一个人对公民宗教不感冒、对公共政治生活就是不参与,又怎么办呢?
卢梭说那就杀掉,因为这个人“违背了社会性的情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社会吧。你看,卢梭的自由,其实就像父母管孩子。为了你好,为了你的自由,我天天跟你唠叨,你要再不听话我就揍你。这么着,越是对孩子好,对孩子下手就越重。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掌权后,搞的就是卢梭这一套。贡斯当说:“法国人想要的自由,你们就是不给;法国人不想要的自由,你们一定要强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卢梭对解放的追求,在法国大革命时却沦为暴力和强制呢?伯林说,卢梭把自由的性质搞错了,他把古代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义务,和自由混为一谈。因而才闹出“被迫自由”的笑话。
那么,自由是不是只有浪漫主义这一个敌人呢?伯林的自由与浪漫的这一对儿概念,又是什么时候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取代的呢?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咱们就开始聊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