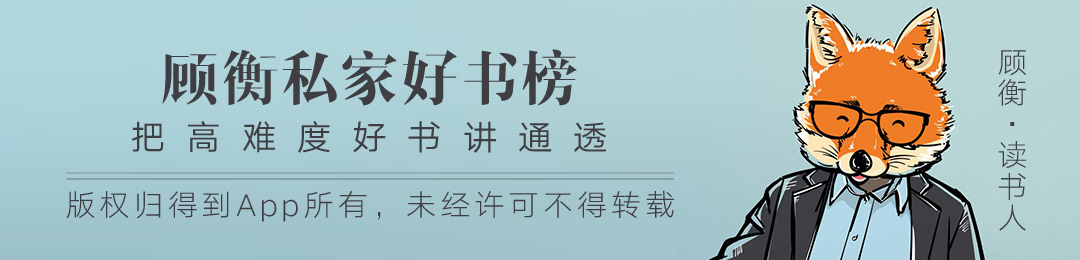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上一期,咱们聊了聊以赛亚·伯林的生平和八卦。自从有了弗洛伊德之后,人物传记的作者就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要给传主来一场精神分析。
叶礼庭也不例外。在《伯林传》这本书中,他总是试图从伯林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性格特点这些东西里,寻找他思想轨迹背后的东西。这种写作方式,虽然有过度解读的风险,但是对我们准确理解伯林,还是很有帮助的。
伯林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上次咱们说了,伯林是一只狐狸,不是一只刺猬。但是在伯林生活的20世纪,却是属于刺猬的。刺猬只关心大事,热衷于观念。
如果刺猬只满足于让它的大事停留在理念的世界,像一道奥数题一样,只是个智力消遣,这很好。但是如果刺猬拿它的大事来改造现实世界,这个伯林就非常反感了。他觉得,刺猬拿大事儿改造世界,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个强盗普罗克鲁斯忒斯,抓住行人就放在自己的床上,人比床长就把人家的腿锯掉,人比床短就硬把人家抻长。
1932年,伯林刚当上牛津哲学教授。当时最大的刺猬,叫逻辑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如日中天。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思是说,一种理论,要么得到经验的证实,要么通过逻辑的检验,否则,它就是不值一驳的垃圾。那这么一来呢,很多哲学上的根本问题,比如,什么是善。这个,经验无法证实,逻辑无法推导,那么,就扫到垃圾堆里去了……如果什么是善都成了伪命题,那哲学这门学科,就成了科学的小秘书。而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看法。
我举一个咱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就是中医,来帮助你理解一下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前面说过,两条标准嘛——要么逻辑说得通,要么能被经验证实。那在他们看来,什么阴阳五行气血两亏的,完全没逻辑。另外谁见过“气”是什么样的啊?这东西也无法证实。所以,中医是垃圾。
但是伯林不这么想。换作他,很可能会说,中医对某些人是有效的,你逻辑解释不了这个现象,那这是你逻辑的问题,不是中医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经验而言,“针灸治好了小明二姨的偏头疼”。这个不是你的经验,而是小明二姨的经验。那为什么,小明二姨的经验,对你们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就不作数了呢?如果小明二姨的经验不能作数,那谁的经验才作数呢?
为了解决小明二姨的头疼传不到维特根斯坦脑袋里的这个难题,逻辑实证主义者只好求助于科学实验方法“双盲对照实验”。如果针灸治疗偏头痛通不过实验,那么,小明的二姨,要么她的偏头疼是假的,要么她的针灸是假的。
你看,强盗普罗克鲁斯忒斯又把他的床搬出来了。
伯林的想法是,我们并不能证实小明二姨的头疼,我们也没必要去证实她的头疼。我们自己头疼过,或者见过别人头疼过,所以能理解小明二姨头疼。这就够了。在生活中,一件事情是因为被我们理解了,所以得到了证实。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想法是反的。他们主张你必须先证实,我才能理解。也就是说,小明二姨必须要先去拍个CT,照出里面鸡蛋大的肿瘤,小明才可以哇地一声哭出来。CT片子出来之前是不能哭的,因为逻辑又讲不通。你哭个啥呢?我觉得,如果世界是按照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想法来运转的话,小明和他二姨,早就断绝一切关系了。
通过和逻辑实证主义这只大刺猬的争论,伯林得出了一个影响他终生的结论,就是:“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观点,能够脱离历史和个人的维度而独立存在。而且,观念也必然存在于和其他观念的关系当中。”
哲学问题,有点烧脑哈。我把伯林的观点再强调一下。两条吧:
- 单纯就观念谈观点没有意义。观念不能脱离特殊的历史,也不能脱离活生生的个人;
- 观念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存在于和其他观念的联系之中。
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思维习惯,让伯林觉得很厌烦。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追求观念的纯粹,而伯林却认为观念必须是连汤带水的,不能脱离与现实的关系,也不能脱离与其他观念的关系。
正好,他这个哲学教授当了没多久,就考取了牛津全灵学院的研究员。全灵学院是全英国公认的顶级学术机构,它招揽一堆聪明人来当研究员,允许他们无所事事,这太适合伯林了。
正是在那里,伯林的学术兴趣从哲学转向了思想观念史。研究观念与现实的互动,研究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成了他终生的学术归宿。
伯林对阿伦特的批评
除了上次说到的男女关系,还有两件事情,特别能说明伯林这只狐狸,反对刺猬仅仅因为逻辑自洽、为了它的大事儿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对生活指手画脚横加干涉。
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二战结束之后,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指责欧洲犹太社区的长老和拉比,认为他们不应该那么懦弱。如果当初他们更勇敢些,对纳粹不是那么配合的话,大屠杀的规模就不会这么大。
虽然伯林的很多亲戚,包括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中丧生,但是他也觉得阿伦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说,“在安全的境况下,无法对处在危险当中的人的行为进行任何道德判断”。
同样的意思,米兰·昆德拉有句话说得更好,更刻薄,昆德拉说:有些人“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动情的”。
伯林很少因为观念之争动怒,对阿伦特是不多的一次。
同样的“狐狸”思维,也体现在他对待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态度上。
伯林对这位著名诗人是最最敬爱的。1945年,他曾去拜访她,这次会面也导致了伯林思想轨迹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当时阿赫玛托娃已经20年不被允许发表作品了,唯一的儿子被关在监狱里。她儿子被抓进监狱之后,她屈服了,违心地写了几首歌功颂德的诗歌。这是她道德上的瑕疵吗?伯林认为不是。
伯林的宗教观
说伯林是一只狐狸,第二个例子是他的宗教观。说实话我就是被伯林对宗教的看法实力圈粉的。所以我也选了一只狐狸做头像,表达对他的敬意。
不信教的哲学家有很多,比较一下他们对宗教的态度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说:
帕斯卡尔说他信上帝,只是一个反讽。他的这个俏皮话,反映的只是他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抖机灵时的洋洋得意罢了。
美国哲学家桑塔亚那对宗教是这么说的:
桑塔亚那对宗教的看法,就像个恋物癖。喜欢女人的衣服、女人的鞋,但他不喜欢女人。
伯林也不信教。他说:
由此可见,桑塔亚那不接受上帝,但这并不妨碍他欣赏宗教艺术。但是伯林却做不到,他认为不理解上帝就没法真正领略宗教艺术的好处。
还是用恋物来打比方,桑塔亚那和伯林都喜欢女人的衣服。桑塔亚那只要衣服,女人是必须缺席的。但是伯林呢,却要求那衣服得穿在女人身上才行。这再一次反映了,伯林要求观念与现实必须要保持“汤汤水水”的亲密关系。
另外,我也很喜欢伯林谦逊的态度。他把自己的不信神比喻为乐盲。也就是说,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神的过错。他也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因为,就像0也是个数字一样,伯林认为无神论也是个信仰,无神论者并没有什么理由在教徒面前滋生出智力上的优越感。
所以,伯林虽然不信上帝,但他一直过宗教节日,也非常尊重教义。他觉得,这些传统、这些仪式,让家人变得更亲密了,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这就够了。至于到底有没有上帝,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期,咱们从观念上,仔细讲了刺猬和狐狸的区别。
伯林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从他对阿伦特的评价、他对宗教的看法都可以看出,他作为一只狐狸,认为观念必须是连汤带水的,不能脱离与现实的关系,也不能脱离与其他观念的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观念史学家,伯林心里是渴望知道一件大事儿的。这件大事儿是什么呢?咱们下期来说。
好,我是顾衡,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