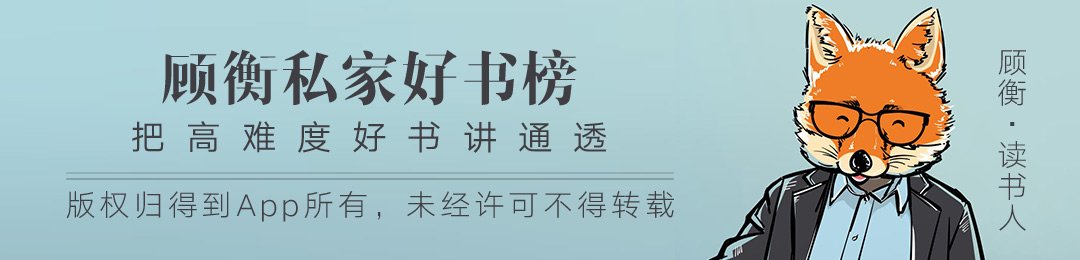你好!我是顾衡。
本周我给您带来的是保罗·莫兰的《人口浪潮》。人口问题,不仅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同时,如何去处理人口问题,也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还是老规矩,在具体介绍这本书之前,咱们就先来讨论一下:生孩子跟国家有什么关系?
人多为什么重要
人口,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它不仅决定了王朝兴替,也是评判帝王功过的核心指标。亚当·斯密就说过:“国家繁荣最具决定性的标志,就是居民数量的增加。”我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也是如此。人口增长,皇帝就觉得自己干得不错;人口减少,皇帝就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就要发罪己诏做检讨。
中国历朝历代用人口来衡量统治的好坏,一是来自于经济上的考量。古代的税赋中,人头税,也就是丁税,一直就是大头。人多,征税就多,国家就强大。
二是,古代皇帝一直以天子自居。贵为天子,他的道德责任或义务,就是所谓遵天命。古人认为的天命怎么体现呢?当然就是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就是女人在家里烙煎饼、奶孩子,大葱和小麦在地里茁壮成长。
人口,在外国也是决定王朝成败兴衰的关键因素。比如古罗马,就是因为人口增长跟不上疆域扩大的步伐,长年征战不休,兵员得不到补充,不得不允许蛮族战士加入罗马军团,效果等于开门揖盗,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雅典也存在同样的人力资源问题。公元前499年,波斯大军入侵,雅典联合了一半以上的希腊城邦,大大小小超过200个,成立了提洛联盟。大家凑份子,拿钱出来一起反抗波斯侵略者。但是把波斯人打跑之后,雅典人却起了贪心,把存在提洛岛的钱搬回雅典,大兴土木,号称要建全希腊最好的学校,要求昔日的战友们称臣纳贡,不服从的就屠城,就把人家老婆孩子当奴隶卖掉。
但是雅典人太少了。当200个昔日战友纷纷背叛雅典,投靠斯巴达之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就胜负已定了。输,对于雅典来说,只是个早晚问题。
不过,要说史上因为人口问题而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造成最大影响的,那既不是光荣的雅典,也不是伟大的罗马,而是斯巴达。
斯巴达先后征服了拉哥尼亚和迈锡尼王国。迈锡尼王国还是它的同祖同宗,都属于多利亚人。在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和斯巴达国王不仅是亲兄弟,还娶了一对姐妹,做了连襟,是标准的亲上加亲。后来,弟媳妇海伦被帕里斯拐走,兄弟俩又并肩作战,打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才又把弟媳妇抢回来。
有着这样的血缘关系,有着这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斯巴达人还要把迈锡尼人当奴隶,这就很不明智。因为你没法让迈锡尼人在精神上臣服你,更何况人家人还多。在斯巴达,奴隶人口最高时达到斯巴达公民人数的15倍。在冷兵器时代,这是个要命的比例。这让斯巴达人一直生活在深深的恐惧中。
斯巴达应对的办法除了全民皆兵,成年男子必须统一住在军营里,难得回家外,另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孩子一出生就属于城邦,是未来的战士。
在斯巴达,对孩子迫切的渴望,导致了斯巴达人古怪的婚姻观。其他地方都是“朋友妻,不可戏”。但是在斯巴达,表达对朋友妻的爱慕却被认为是恭维而不是冒犯。这种事情就算真的发生了,大家也都不以为意。孩子只要是斯巴达城邦的血统就行。至于具体是哪个男人的,这就不那么重要了。
斯巴达这个把媳妇当共享单车的习俗,除了出于恐惧而渴望孩子这个现实原因之外,还有观念的影响。
那时候的人也讲究优生优育,但是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更加优秀呢?那就得多个父亲一起合作。三个男人合作能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那三个男人一起当父亲呢,那他们的孩子力气也会更大。
希腊神话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宙斯、波塞冬和赫尔墨斯三位大神闲逛,在底比斯遇到了一个叫海尔瑞斯的老头,老人家虽然一贫如洗,却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三位大神出于感谢,说可以满足老人一个愿望。海尔瑞斯就说了,想要个儿子。于是,这三位神找了张生牛皮,一起射精在上面,把牛皮包起来埋在地里。
九个月后,从地里蹦出个男孩儿。他就是全希腊力气最大的俄里翁。电影《超人》开头,超人的亮相就借鉴了这个神话情节。区别只在于在《超人》中,小孩儿是从天上飞来的,俄里翁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斯巴达的这个婚姻观,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专门为斯巴达人设计了一个角色,叫护卫者。这个护卫者,既承担了保卫城邦的责任,也负责政令的执行。有点儿像咱们国家先秦时期的“士”。
柏拉图说“护卫者”既然负责公共事务,就必须要杜绝私心。那一个人怎么才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就是两个办法,第一不许有私人财产,第二不许有孩子。
咱们五代十国的时候,南汉后主刘鋹也考虑过怎么杜绝当官的有私心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当官的必须阉掉。文武百官,总共阉了两万多人。但效果却非常不好。没几年,他就被赵匡胤灭了。看来刘鋹的办法不行。
柏拉图的办法就不一样。他允许护卫者有孩子,但不能让父母识认出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说,护卫者阶层是共享妻子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抱走,由所有哺乳期的妇女集体喂养。这么一来,不仅爸爸是谁搞不清楚了,连亲妈是谁也没人知道了。
“公共丈夫”和“公共父亲”
柏拉图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还在产生重要的影响。就是:一个孩子,是向下属于父母,还是向上属于城邦?这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咱们拿时间上差不多的秦国商鞅变法和斯巴达来做个比较:
中国的战国时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树状的、一层一层的宗族结构。国君作为树干,可以号令自己的兄弟、叔叔之类的主要分枝,但是国君不能向分枝的分枝直接发出指令。举例来说,就是他可以向弟弟发出指令,但没法直接下命令给他弟弟的家臣。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打破宗族,成立一夫一妻小家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组织扁平化呗。他颁布法律规定:家里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却不分家的,人头税按五倍征收。
把宗族结构拆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国王把他的国民分为两等,第一等是成年男子,国王和他直接立约,然后国王把妇女和儿童作为第二等国民,“委托”给成年男性统治。就这样,秦国实现了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逐渐转变,消灭六国,实现了统一。
从秦以后,中国历朝历代都大致延续了秦制,就是把打压豪族,扶持小家庭作为基本国策。这样的国家,像个“丈夫俱乐部”。就是丈夫们向国家效忠,而作为回报,国家为所有的丈夫出头,支持他们在家里对老婆孩子的绝对权威。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公共丈夫”。
而斯巴达,因为城邦太渴望孩子了,所以它是轻家庭而重孩子的。在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很高,人们也并不看重女性的贞操。也就是说,只要孩子是斯巴达血统就行,至于具体是哪个男人的,那并不重要。男人的重要性被削弱后,由城邦为孩子提供统一的教育和抚养。这样的国家,就像所有孩子的父亲,所以被称为“公共父亲”。
公共丈夫型的国家,会倾向于孩子属于父母,国家就不应该管,或者少管;而公共父亲型的国家,会倾向于孩子属于国家。如果有妇女儿童受虐待了,国家就会积极介入,越过丈夫,直接为妇女儿童提供保护和帮助。
追溯历史源头,在人口策略上,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策略的分歧。比如想让国民多生孩子。公共丈夫型国家会倾向于帮男人,也就是给一家之主的男人减税,让他有钱多买奶粉;而公共父亲型国家倾向于越过男人,直接向妈妈和孩子提供补贴。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也会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影响。
今天我们简单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口问题决定了古代王朝的兴衰——历史上疆域扩大过于迅速的王朝,往往因为人口增速跟不上而崩盘。除了雅典和古罗马,莫兰在《人口浪潮》中说,大英帝国曾经不可一世,号称日不落帝国。也是因为人口跟不上,沦为二流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古代社会有公共丈夫和公共父亲两种类型的策略,因而造成了极为深远的社会影响。
好,我是顾衡。明天,我们回到正题,说说保罗·莫兰在《人口浪潮》里都说了些什么。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