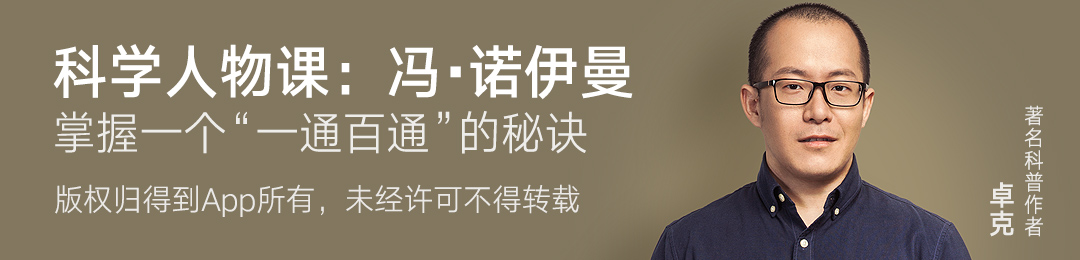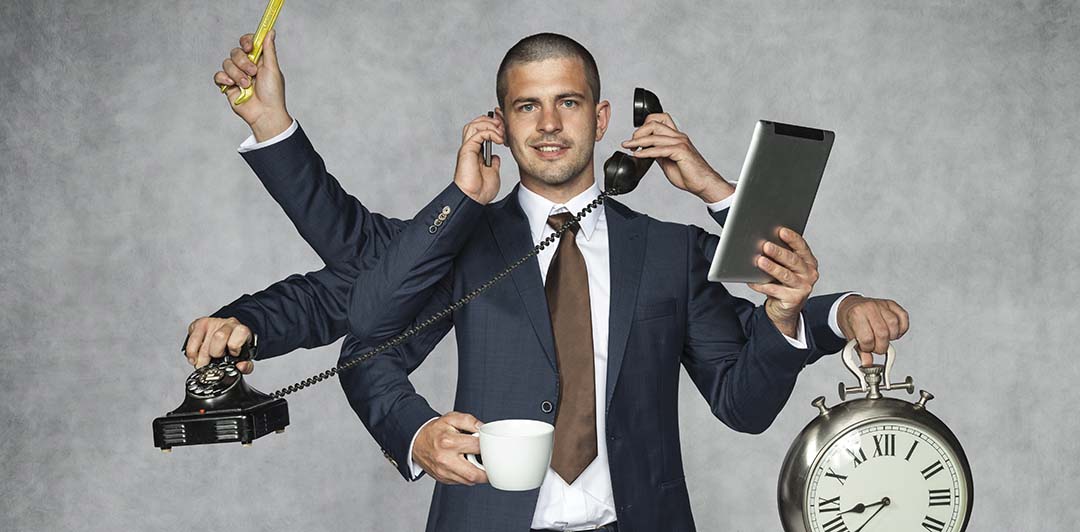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如果去数一数冯·诺伊曼的头衔,你可能会眼花缭乱。他在1948年到1950年间,一共给6个官方机构担任过顾问,同时还担任了另外6个民间智库的顾问。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冯·诺伊曼超级顾问的职业生涯,然后再谈谈他为什么能接受这样一种超负荷的生活。
眼花缭乱的顾问头衔
对于有些名人来说,12个顾问可能不算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实际上并不做任何工作,只是挂一个头衔而已。
但冯·诺伊曼却是真顾问,主要负责解决那些机构里的科学家也搞不定的东西。但那些难题对冯·诺伊曼来说,大部分都是小菜一碟。比如IBM对这个顾问的全部期待就是——请冯·诺伊曼教授把他每天早上洗脸刮胡子时,脑子里冒出的新想法告诉他们。
我们来仔细梳理一下,冯·诺伊曼一生担任过的职位。
最早是在1933年,他获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职。这是他的全职工作,兼职的顾问包括——
能让这么多机构同时聘用已经实属难得,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能让各个机构都满意。尤其是我刚刚最后提到的两个单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泰勒实验室,而且这两个单位彼此间的矛盾还非常深。
当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在1951年3月份和实验室主任布拉德伯里(Norris Bradbury)关于氢弹下一步应该怎么设计,吵到了完全没办法继续合作的地步。最终,泰勒拍拍屁股走人,并凭借自己和军方的关系申请了第二个实验室,也就是劳伦斯-泰勒实验室,目的就是要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竞争。
第二个实验室建成后,马上就聘冯·诺伊曼担任科学顾问。于是,冯·诺伊曼就在竞争关系的夹缝中,为两个实验室不同的氢弹发展方向同时提供协助。最后的胜者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但双方没有任何一个对冯·诺伊曼有意见。
冯·诺伊曼自己说,这是他在研究计算机的过程中经历过的事情,一旦第一步突破实现了以后,竞争才是推动新科技发展的最好方法。媒体评论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时也说:“要不是泰勒从原来实验室出走,可能氢弹还要再等几年才会成功,竞争让速度加快了。”
担任十几个顾问的工作,冯·诺伊曼都解决什么问题呢?比如说——
每一个问题都是极为现实的,要么是和资金紧密相关,要么就是和人命紧密相关。在这些问题上,大家都愿意听冯·诺伊曼的分析。
对冯·诺伊曼一生的顾问工作,最感恩的是IBM。当然客观的说,IBM也是受益最直接、最多的。“氢弹之父”泰勒就曾经这么评论过:“IBM至少应该把一半的股票送给冯·诺伊曼。”
自从冯·诺伊曼去世后,IBM每年都会给斯隆基金会拨一笔钱,资助那些为冯·诺伊曼写传记的人,一直资助了30多年。按说冯·诺伊曼的传记应该是最多的,可无奈的是,大多数传记作者都是数学家、物理学家,他们都在深挖冯·诺伊曼的研究细节。而这些内容,别说普通读者看不懂,甚至连方向不同的其他科学家也看不太懂,所以上市的数量就很少。
工作和生活日常
担任十几个顾问的工作,冯·诺伊曼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工作上大概是这样——
比如从华盛顿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路上,他会在飞机上把前一天陆军特种武器会议上讨论的关于“火箭弹的火药如果用锥形填装会产生什么爆炸效果”计算出来,然后再琢磨一下“埃克特设计的水银延迟线做的内存怎么编码成二进制”。
在汽车上,把2小时后的会议发言准备一下。车门一开,他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时候已经有好几个工程师等在走道里了,他们知道今天下午冯·诺伊曼会来。其中有一个工程师忍不住把准备好的问题递给冯·诺伊曼,冯·诺伊曼在打招呼的间隙低头看了看问题,并在走进会议室之前,掏出笔在纸上把解法大致写下来,然后就进去开会了。而那个工程师看着这张纸条上的解答,心满意足。
生活中——
他的妻子克拉拉说:
“白天约翰尼如果在华盛顿工作的话,晚上就会回家,但会有很多其他领域的科学家来拜访,我就是他的夜间秘书,帮他款待客人。等到一般人都睡着的时候约翰尼也会躺下,不过对他来说睡觉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相信数学是在潜意识里研究的。他会带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入睡,早上3点钟醒来时往往就有答案了,然后他走到桌前给同事打电话。打完电话他就去书房工作到清晨,等天大亮了就云雀一样快活的上班去了。”
重要原因:天性和习惯
虽然冯·诺伊曼的头衔令人羡慕,但这种生活节奏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吃得消。而对冯·诺伊曼来说,为什么能做到驾轻就熟呢?
其实这就是他的天性,他就喜欢热热闹闹、乱哄哄的气氛。
小时候家里吃晚饭时,常有各国银行家、企业家来访,而小冯·诺伊曼肯定会出席,听大人们谈商业合作。他并不是被强迫这样做的,而是本来就很喜欢这种热热闹闹、迎来送往的生活。他的妻子说,虽然家里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安静的书房,但冯·诺伊曼总是喜欢一边放着音乐、一边在客厅琢磨问题,好像不乱一点他就没法工作。
冯·诺伊曼也把这种习惯带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招到了爱因斯坦的厌恶。其实何止是爱因斯坦,高等研究院其余所有人的风格都和冯·诺伊曼的性子截然相反。
外人觉得高等研究院高深莫测,但内部人士对这里的评价是偏负面的。因为对于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来说,这里实在像一座集中营。
物理学家费曼就曾经评价过那里的教授:“那些可怜的家伙本来完全有机会做点什么,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相信这种情况会让他们愧疚并且在体内长出蛀虫,他们开始担心怎么还是没有灵感,但没办法,就是没有灵感。”还有数学家回忆那里的生活:“一般人一辈子才能学会的数学,他们那里的教授只用早上几个小时就全能搞定了,余下所有的时间就用来找别人的茬。”
冯·诺伊曼在接任顾问之前,在高等研究院的全职工作确实是比较憋闷的。
如果统计他1930-1940年在高等研究院这10年内的论文,他一共发了36篇。对高等研究院内部来说,已经是极为高产了。但他在还没入职高等研究院之前的1929年一年,就发了32篇论文;再之前的2年,也一共发了高达34篇论文。
他自己也认同外界对高等研究院的负面评价——“一所诱惑极少数贪婪的学者走到死胡同去的高薪研究院”。
为了排解这种郁闷,冯·诺伊曼的做法就是每周末在家里搞Party,政界、商界、文化界,当然也有科学界的名人都来到这里。这个聚会在1930-1940年的十年间,一度承担了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那些刚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犹太科学家,在这里找到未来的老板。
可能的原因:短睡基因
除了生活习惯和爱好之外,最近的一项科学研究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冯·诺伊曼这样的人会有这么充足的精力,那就是短睡基因。
至今为止,生物学家发现了2个和睡眠时长高度相关的基因,它们分别是ADRB1和DEC2基因。如果这2个基因发生了突变,人们需要的睡眠时间就很短。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天平均需要8小时以上的睡眠;而拥有短睡基因的人,平均一天只需要睡6小时,有些人甚至常年只需要睡4小时就够了。再让他们多睡也睡不着,完全是一种煎熬。
这些人的健康程度和普通人没有差异,而且记忆力更好、精力更充沛、对疼痛更不敏感。虽然没有人检测过冯·诺伊曼是否有这样的基因突变,但我猜他就是这样的人。
睡眠更短、记忆力更好、精力更充沛,这些自不必说。连对疼痛的忍耐力,他也是不一般的。1955年5月,冯·诺伊曼就感觉到了左肩锁骨的剧痛,一直拖到了8月才去照X光,结果发现是肿瘤。于是,马上就进行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又开始工作了。直到10月28日,还在国会、自然科学基金会、五角大楼、普林斯顿到处开会。
直到把手中大部分事情处理完,也就是11月初的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里站不起来了。换句话说,他忍耐了半年之久的剧痛,而这期间工作节奏完全没有乱。
不过如果这真的是基因优势,我们也羡慕不来。目前科学家估计,短睡基因的人群占比大约是1/1000,而且这个比例已经比随机突变要高很多了。
之所以拥有短睡基因的人会被筛选出来、变得越来越多,是因为环境出现了两个剧变,一个是电灯的出现,一个是智能手机的出现。这样短睡节省出来的时间,就可以用来增加自身竞争力。而从前,即便这些短睡的人睡不着,也干不了太多事情。
也许,当人类解决夜间照明问题5万年之后,大部分人都会拥有短睡基因,成为接近冯·诺伊曼那样的人吧。
下节预告
下一讲,我给你讲冯·诺伊曼人生的最末阶段,也就是他被诊断出骨癌之后的事情。这样一个天才,会怎样面对死亡呢?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