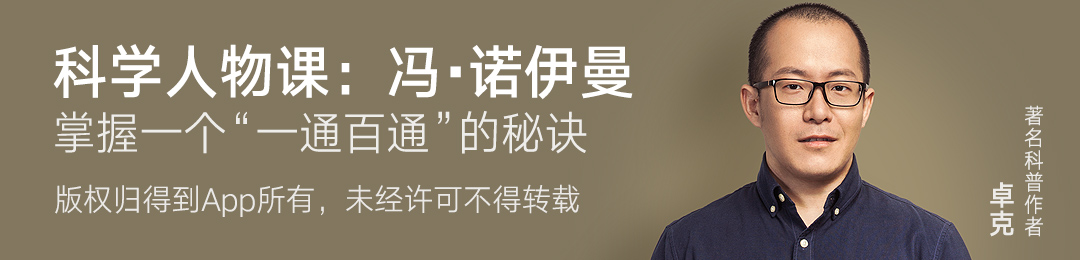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一个历史功底雄厚,又善于计算博弈问题的精明犹太科学家,对使用核武器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等同于问冯·诺伊曼对使用核武器是什么态度。答案就是,毫不犹豫的用核武器打击对手,坚决反对绥靖政策。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冯·诺伊曼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来源。
原子弹诞生前的理论突破
核武器的诞生,其实来自于一连串的物理学突破:
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证明了中子的存在,3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2年同年,考克克劳福特(Cockcroft)和沃尔顿(Walton)使用质子轰击锂,完成了第一次人工核反应。
1934年,物理学家西拉德(Szilard),也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和冯·诺伊曼一同就读于路德中学的同学,受到人工核反应的启发,提出了由中子诱发的链式反应。
1939年1月,德国化学家哈恩(Otto Hahn)和物理学家斯特拉斯曼(Friedrich Strassmann)详细研究了铀原子核裂变的现象。
1939年9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在哈恩的研究基础上指出,同位素铀235是最合适发生由中子引起的链式反应的。
到了玻尔这一步,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原理已经齐备了,不过一些物理学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比如,苏联物理学家伽莫夫(George Gamow)就给后来的“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打电话说:“玻尔是不是已经疯了?他居然说中子可以分裂铀。”泰勒听完这个说法,马上联想起了最近一系列让自己费解的实验,那些实验是由费米(Enrico Fermi)做的,结果他突然明白,人类是可以释放原子核内的能量的。
而费米更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刻,就用手比划了一个足球给办公室的同事们,然后说:“像这么大一个原子炸弹,就足可以让整个纽约灰飞烟灭。”
曼哈顿计划与原子弹的诞生
很多最早听说链式反应的物理学家,马上就意识到了它的战争价值。
刚刚,我梳理过原子弹之前的物理学成就,其中第四步进展是由德国科学家完成的。所以想让德国人对原子武器的价值一无所知,是不可能的。欧洲科学家中,反应最快的是3个人——西拉德、维格纳和泰勒。三个人都是冯·诺伊曼在路德中学的同学,他们连同冯·诺伊曼被称为是“匈牙利帮”。
对于核打击,“匈牙利帮”是持积极主动态度的。于是这3个人一起去拜见爱因斯坦,目的只有一个——自己人微言轻,而爱因斯坦德高望重,所以想请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让他务必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
爱因斯坦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写信催促罗斯福总统。但是,这封信竟然被一个平庸的家伙当作绝密文件锁在了保险柜里。直到英国战争委员会以官方身份提醒美国重视研究原子弹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出来。这时候,已经2年过去了。
冯·诺伊曼作为高等研究院的杰出代表,马上就同意参加原子弹的研发工作。
其实,就在军方找冯·诺伊曼之前,关于是否要研发核武器摧毁敌方,科学界就已经出现了分歧。你想,高等研究院最闪闪发亮的明星是爱因斯坦,连冯·诺伊曼都找了,还能不找他吗?确实也找了,但是爱因斯坦婉拒了。
1942年底,原子弹计划破土动工,由奥本海默领导研发上的全部工作。在外界看来,当时美国几十位杰出的物理学家都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其实,他们都秘密的到了沙漠边缘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参与原子弹的研究。
对待核武器的不同态度
可一旦战争结束,不同的态度马上就又显现了出来。爱因斯坦发表文章说:
“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把它递到了另一个疯子手里。”
凭良心说,爱因斯坦这话有点假。因为导致美国决定先把原子弹制造出来的,是英国官方的催促。他的那封信被封存了2年,压根没被重视,而且他全程也没有参与过原子弹的研发。
但领导原子弹研发的奥本海默的忏悔就不一样了,他在其中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1945年10月25日,杜鲁门总统接见这位美国国家英雄。刚寒暄完,奥本海默就坦言:“我觉得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杜鲁门说:“血在我手上,让我操心这些事儿吧。”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据说后来杜鲁门告诉国务卿,今后再也别让他见到这个家伙。
其实,奥本海默的忏悔并不是个例,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大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有负罪感。有些人早早患上了癌症,临去世的时候还觉得这是他们的报应。
但冯·诺伊曼和这些人都不一样,他的态度是——
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垄断核武器的使用权。科学技术是中立的,怎么使用和控制不是科学家决定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所以科学家不应该有什么负罪感,那样自责就太高估自己了。
他甚至还评论说:“这些人只是表面装出来的负罪感,因为这样做他们可以收获更多的信任。”在接受LIFE采访的时候,冯·诺伊曼还这样回答过:“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明天不用原子弹轰炸他们,我要问为什么不是今天就去呢?如果你说今天5点就去轰炸,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不是今天1点钟就去呢?”
和冯·诺伊曼持相同意见的人不多,除了匈牙利帮的几个人外,就只有数学家罗素了。这些激进的战争支持者在战争结束后第四年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苏联也引爆了他们的原子弹,而且技术还是从曼哈顿计划中偷来的。
于是,马上研制一个比原子弹更具威慑力的武器就成了重要任务。冯·诺伊曼、泰勒、乌拉姆、西拉德这些人经过5年努力,终于在1954年3月1日,成功的在比基尼岛上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威力是第一颗原子弹的500倍。
原因一:思维惯性
可能很多人想不通,冯·诺伊曼这么一个胖墩墩的老好人,任何时候都避免和人发生无意义冲突的精明科学家,为什么在涉及人伦道德的问题上会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而且还毫不掩饰呢?
有一种解释有些道理,那就是他的逻辑思维惯性。
别忘了,冯·诺伊曼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和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高度吻合,并不是偶然。他们都可以做到完全剥离情感因素,运用纯粹理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世界上没法共存两个超级大国,先发制人、彻底摧毁对手是这场战争的最优解。
罗素在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个判断过程:“对于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我已经提出的理由就像数学证明一样明白无误,不可避免。”
我们确实可以这样理解他们:人的大脑在做决策前,负责传递情绪冲动的边缘神经系统和负责做理性判断的前额叶,都在为最终的结果投票。至于哪一方能赢,就要看这是一颗怎样的大脑。
由于这几十年来,他们两人的大脑一直在做严谨的逻辑分析,前额叶得到了空前的高强度训练,所以就会在决策投票中占了优势。别看这个决定客观上会造成大量死亡,但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人。他们可以清晰地把握这一点,而不受情绪的影响。
原因二:对战争的痛恨
这个说法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但它解释不了一个现象: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其他科学家,在理性判断上的能力也都是万里挑一的水准,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的判断呢?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冯·诺伊曼本人身上寻找原因。
其实答案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苏联对匈牙利的占领,深深刺痛了冯·诺伊曼的心。“为什么不是1点轰炸,而要等到5点才轰炸”的判断,显然不只是前额叶理性的投票,更是大脑边缘系统情绪冲动的投票。
听完前面几讲的内容,你脑子里的冯·诺伊曼应该是一个灵活变通、智商情商超群的人,好像从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挫败,也从不表露自己的情绪冲动。确实,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柔软的东西。
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不怀念欧洲,因为每一个熟悉的角落都让我想起那时候的世界、那时候的社会、童年时激动人心又模糊的愿望,以及这些不能带来安慰的废墟。我不喜欢欧洲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不愿意回忆起1933-1938年9月间,留下的关于人类尊严幻灭的所有记忆。”
他的女儿对这段话有个评论,她说:“欧洲的这段历史给父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他表面上谈笑甚欢,下面却隐藏着颇为玩世不恭、悲观厌世的世界观。”
要不是他女儿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估计谁也不知道冯·诺伊曼在二战开打以后对世界是如此的失望,以至于到了厌世的地步。
再结合他在二战开打前的生活安排,还真能联系起来。
冯·诺伊曼比所有的欧洲科学家都更早来到美国,有高工资和优越的待遇,按说就踏踏实实移民美国吧?不,他从移居到美国起,每年仍然保持着4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欧洲游学、演讲、度假。直到最后匈牙利进入战争状态,再也不能回去为止。
想来,20世纪20年代多样性那么丰富的布达佩斯、哥廷根、阿姆斯特丹、柏林,一定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加上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超强的记忆力,这些美好的感觉在他心中一定是有倍增效果的。在精通欧洲史的情感基础上,如果沉浸在1938年之前的欧洲,那不知道会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体验、多么强烈的幸福感。而二战和战后苏联的占领,不但从现实世界里摧毁了一切,也从历史上制造了不可挽回的割裂。
所以,冯·诺伊曼这种激进的主战态度,既是他理性的判断,更是他情感上的“恨”所共同决策出来的。他和普通人一样有情绪冲动,只不过埋藏得有点深,表现得很隐晦而已。
下节预告
除了帮助军方研制核武器,冯·诺伊曼一生中还担任过很多机构的顾问,帮这些机构解决它们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难题。下一讲,我就给你讲讲冯·诺依曼另外一个重要身份——超级顾问。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