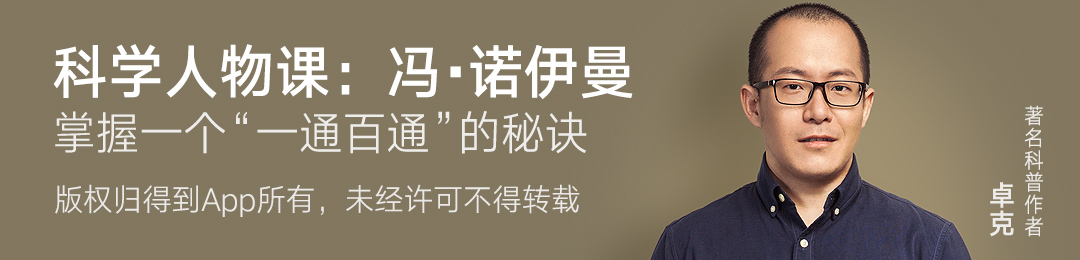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如果抛开学术部分去看冯·诺伊曼,他和其他伟大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那种灵活变通、八面玲珑的性格。单纯从做事风格上看,甚至可以说,他就像是一个政商界的老油条。
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冯·诺伊曼身上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天才的典型形象
一个天才人物,最容易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来自别人的嫉恨了。有的时候是因为天才闪闪发亮,一些内心自卑的人会不经意间生出嫉妒;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天才本身狂傲自大,谁也看不上,和人交流的时候把人得罪了。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几个科学圈的例子:
比如加州理工大学的盖尔曼,又被称为“夸克之父”,如果他听到演讲者讲的东西不重要或者仅仅是没意思的话,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一份报纸开始看。因为他是诺奖得主,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往往就坐在第一排,所以这么搞就让演讲者很下不来台。这就是一种学术能力加智力水平的双重鄙视。
当然,盖尔曼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被鄙视的年轻人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但客观上说,这样的做法是会让人看不惯的。
还有像物理学家泡利,如果他听到了不认同的观点,会在第二秒马上站起来开怼。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在爱因斯坦的演讲上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从最后一排站起来,用连珠炮似的问题让爱因斯坦听得汗都下来了。
这么不留情面的做法差不多都是针对敌人才会用的。那爱因斯坦在泡利心中是老顽固和学阀吗?当然不是。泡利曾经把爱因斯坦比喻成物理学界的国王,把他自己比喻成国王的长子。但对这样一个自己非常敬重的科学家,泡利也是一言不合就大动干戈。
事实上,泡利也曾经用同样粗鲁的方式对待过比他小20多岁的杨振宁。在杨振宁的一次演讲中,泡利连续打断了他好几次,到最后杨振宁甚至已经讲不下去了。幸好有奥本海默圆场,最后才勉强讲完。
实际上,那次暴跳如雷的泡利确实是抓住了杨振宁理论上的缺陷。但一个对自己的自信有所克制的人,就算是当场提意见,也不会把一场演讲弄到几乎要黄了的地步。
灵活变通的冯·诺伊曼
说完这些,如果我们再对比看冯·诺伊曼是如何对待枯燥乏味的演讲的,你就会发现他的情商有多高。
当冯·诺伊曼听到一个乏味的演讲时,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表现出丝毫能被人察觉到的不满意。相反,他会开始在脑中计算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并且在思考的同时用手遮着嘴、微微皱眉,眼睛望向演讲人的方向。看上去好像是对演讲者的内容若有所思,其实思绪早就不在这里了。
有一次演讲,台上的教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后来在问答环节,很多同行都针对这个错误一直追问,结果竟然被这个教授糊弄过去了。晚上聚餐时冯·诺伊曼说,只需要问这个教授3个问题,他的整个发现就会土崩瓦解。别人听了就很好奇,你当时怎么不问呢?冯·诺伊曼说,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下不来台不是太不好了吗?反正你们和他自己都知道其中有错误。
恃才傲物是天才主动发起的攻击,可如果是别人向天才发难,尤其是在学术上发难,怎么办呢?有人说,当然是反击回去,让对方哑口无言。但冯·诺伊曼也不是这样做的。
当他在表达一个观点或者陈述一个理论的时候,如果对方反对并且表现出激动的情绪,冯·诺伊曼马上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和对方讨论了,而是会用几个和刚刚讨论的内容有关的黄段子过渡一下,气氛马上就缓解了。
过于锋芒毕露,就会招致小人的打击报复。比如刚才说的在泡利发难时帮杨振宁打圆场的奥本海默,他本人就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典型,前半辈子得罪的人太多,以至于战后被人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陷害得很惨。
而冯·诺伊曼和周围的很多人都相处得特别好,完全没有陷入到这些麻烦之中。
他这种能力不是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学会的。其实从孩子的时候起,他就明白这一点。
上学时,当一个难题出现,在同学们都没算出来而只有他算出来的时候,他也不会着急忙慌地炫耀,知道解法又能怎样呢,他只会笑眯眯地看着大家而已。
这种变通和灵活,在他选择工作上也是如此。
1929年,冯·诺伊曼面临就业问题。实际上以学术水平看,他早就超过不知道多少教授了,但却只能以无薪讲师的身份边教课边等待空缺出来的教职。
难道不能去其他国家吗?可以,但欧洲其他国家情况也大都类似。当时,只有美国大学的教授职位有空缺。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世界科学中心,属于二流人才才会去的地方。
冯·诺伊曼当时调查了一下,德国在3年内大约会空出3个教职,但现在至少有40个无薪讲师等着竞争。所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发来offer,他马上就同意了。到了美国,他觉得这里的人都很务实,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的文化,就干脆把名字“雅诺斯”改成了“约翰”,但为了标榜自己家曾经的贵族身份,冯(von)姓还特地保留着。
当时欧洲很多著名的科学家犹犹豫豫,不愿意去美国,和冯·诺伊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如外尔(Hermann Weyl)这位著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打算在自己退休后让他接班,所以他就一直舍不得彻底离开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答应给他一笔巨额收入,他的态度才松动了。但刚刚接受了offer后又反悔了,还是想留在哥廷根。但刚把offer拒掉,希特勒就在竞选中胜利了。他一看形势不好,又求着高等研究院重新聘用他。
而冯·诺伊曼不是这样。他早早就看出欧洲形势不妙,在1929年就离开了,属于最早一批逃离欧洲前往美国的科学家。这个时期,美国大学教职多,资金也充裕,所以他的待遇一直很好。而很多开战后才逃亡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就轮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了。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很多人可能会说,听你这么一讲,冯·诺伊曼不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谁都不得罪,既圆滑又会利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对大局做判断,甚至对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什么留恋。
其实不是的。
他不和人争吵的根源是,争吵并不会改变那些人的观点,而只会徒增矛盾。所谓“不和傻子吵架”就是这个道理。
而改名字,也并不意味着对自己民族认同的冷漠。
其实像东欧这样文化交汇处的人,并不会觉得“雅诺斯”和“约翰”有什么本质区别。“约翰”这个名字来自于古老的希伯来文,在匈牙利语中是雅诺斯(János),在英语中就是约翰(John),在德语中是约翰尼斯(Johannes),在意大利语中是乔万尼(Giovanni),在西班牙语中是胡安(Juan)。这就有点像我们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异那样。
但是,在那些通过圆滑无法解决矛盾的场合,冯·诺伊曼会挺身而出。但这种挺身而出并不是硬扛,而是利用一切技巧获胜。
比如,我前面已经举过的一个例子:当年ENIAC团队的工程师计划把计算机的各种设计注册专利,好发展自己的创业公司。冯·诺伊曼觉得这种方法非但不能让他们的创业公司成功,反而会导致计算机技术发展变慢,所以就使出了一个杀招——和这2位工程师的领导联手,把设计思路写成了一份101页的报告公布了出去,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竞争。
这可是实实在在得罪人了,甚至可以说是断人财路,但冯·诺伊曼不这么认为。因为当时所有的好想法都会在几年后变得面目全非,它们真的不值钱,凭借这些支撑不了一个公司的创生和发展。可提前注册专利、设置门槛,却会妨碍别人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所以,既然和他们对抗才是全局最优解,那就正面对抗。
除了这件事,还有一个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冯·诺伊曼简直就像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
那是在冯·诺伊曼为氢弹项目做顾问的时候,遇到了计算机性能上的瓶颈。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国家经费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多了。
他想制造更好的计算机只能和高等研究院说,但院长艾德洛特委婉的提出了几个困难:第一,这里常年以来就只是思想的乐土,而不是搞什么大型实验、制造大规模设备的地方;第二,一年10万美元、总共30万美元的研发预算,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冯·诺伊曼听出了拒绝之意,没有再做任何解释就感谢了院长大人。结果他转身就写了五封信,分别是给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和IBM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去你们那里工作。每个单位收到来信都欣喜若狂,马上和冯·诺伊曼联系,商量细节,然后都发来了年薪不低的offer。
接着,冯·诺伊曼把哈佛的offer给芝加哥大学看,把芝加哥大学的offer给IBM看,再把IBM的offer给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看。5个机构为了争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轮番加价,最后哈佛大学出价最高。然后,冯·诺伊曼拿着最后这个经过轮番抬价已经高得不得了的offer给同事们看,意思是说,我要离职了,真舍不得和你们一起奋斗的日子啊。
这些教授们一听冯·诺伊曼要走,这是高等研究院的巨大损失,于是一起给院长写联名信挽留。最后,院长拿冯·诺伊曼实在没辙,只能说:好吧,你去造你心中的那台计算机,我给你找钱去。
在这些冯·诺依曼挺身而出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明的侠客,不会浪费体力和人鏖战,更不会胡乱牺牲自己,只在最关键的时候仗剑当空,一击致命。
而这些沟通中的高级技巧和“阴谋诡计”是冯·诺伊曼独有的,更是很多死脑筋的学者应该补足的。
下节预告
和顾及他人感受的特点相对,冯·诺伊曼却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主张毫不犹豫的用核武器打击敌人。为什么他会呈现出这么矛盾的态度呢?下一讲,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个问题。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