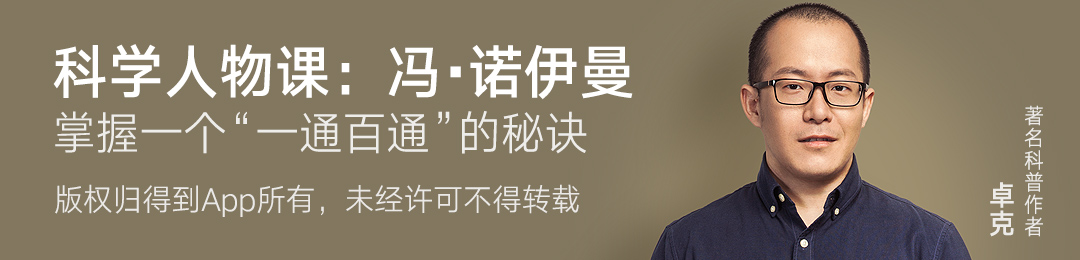你好,欢迎来到《科学人物课:冯·诺伊曼》,我是卓克。
在具体讲冯·诺伊曼的科学成就之前,这一讲我们先说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
冯·诺伊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科学家呢?和其他的科学家相比,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跨领域终身高产
上学时,导师曾经给我做过一个比喻:
科研中最牛的人,比如杨振宁先生,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呢?就是设计出一件衬衫,然后这件衬衫能穿。
次一级的,比如那些院士们,他们是在衬衫左上方设计一个口袋,发现这里可以装名片,可以别钢笔。
再次一级的人,就是我导师那样的人了,他们发现衬衫左上方的口袋可以装东西,于是就在右上方也设计一个口袋,也可以装东西。
而再次一级的,就是还没有资格带硕士和博士的那些科研工作者,他们做的工作往往就是,发现原来我们可以往衣服上缝口袋,于是赶紧在衬衫后背比较宽敞的地方也缝上一个口袋。
比这个还差的,就是发现原来在衣服上缝口袋有利可图,那为了省事儿,不缝了,干脆双面胶贴一个算了。
还有一些怎么都憋不出成果,可又不想造假的硕士、博士们为了毕业,会在论文里像模像样的讨论一下,当一个人倒立行走的情况下缝的口袋必须口朝下的必要性。
这大致就是学术贡献按等级排下来的逻辑。在这种比喻下,冯·诺伊曼的成就是什么样的呢?
他一生不仅设计了衬衫,还设计了毛衣、围脖、帽子、领带、手套、运动鞋等东西。这些东西就对应他在集合论、量子力学、计算机、博弈论、经济学、流体力学、数值分析等领域中的贡献。
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因为20世纪以后,学科分支细化了,一个不起眼的细小分支就能耗费一个天才的一生。而冯·诺伊曼一个人却能在十好几个领域都做出重大成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这些成果还在不断涌现。
相当多的科学家,哪怕是特别伟大的,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往往在30岁之前就做出来了。爱因斯坦和牛顿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如果30岁还没有杰出的成果,那很可能一生都不会有太大希望了。而冯·诺伊曼不同,这些成果是伴随他一生的。
关于冯·诺伊曼的学术成果,我们后面会分几讲挨个说。这一讲先说说他这种终身跨领域高产的特点。
数学和化学的学习
为什么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大都不是这种跨领域终身高产的模式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冯·诺伊曼不会被一些执着的欲望控制住,总能和它们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
这一点,从他上大学时就表现出来了。
17岁时,冯·诺伊曼要考大学。父亲对这个事儿很是上心,甚至找来了路德中学的大学长,也就是后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向他征求报考专业的意见。最后共同商定,报考化学专业。
但咱们之前说过,冯·诺伊曼在路德中学的校长,也就是那位体育老师,专门请大学老师给冯·诺伊曼开小灶,讲更深的数学课。所以虽然家里给的专业意见是考化学,但数学才是冯·诺伊曼的最爱。所以结果他同意了家里的决定,只不过细节上有点复杂——
先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两年化学,但这两年是不拿学位的,只是作为一个过渡。两年后再以此为基础,去报考瑞士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化工专业。与此同时,他还注册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需要在这两年里学习很多硕士阶段的专业课。
也就是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是两年后才需要常去的,在这两年时间里,冯·诺伊曼要先应付柏林大学的化学课和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课。
按说课业负担已经挺重了吧?但冯·诺伊曼也没有经常待在在柏林和布达佩斯,他只是晚上写写这两所大学的作业,然后每个学期末参加考试。
那冯·诺伊曼去哪儿了呢?
他经常跑到德国的哥廷根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为什么去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是跟着两位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和布劳维尔(L.E.J.Brouwer)学习数学去了。当时,希尔伯特在哥廷根大学,布劳维尔在阿姆斯特丹大学。
听到这里估计你会觉得,冯·诺伊曼这是在和爸爸斗心眼呢吧?嘴上说是学化学,但实际却阳奉阴违跑到德国和荷兰学数学去了?
其实不是。因为两年后,他一次就考上了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不但考上了,而且因为成绩太出色了,所以还跳了一级,直接从化学专业的大二开始上。要知道,这个学校是欧洲出了名难考的。26年前,爱因斯坦考了两次才考上。
不过即便考上了,冯·诺伊曼也几乎没在苏黎世长待。而就算是仅有的一些待在苏黎世的时间,他主要也是在外尔和波利亚这两位数学家的教室和办公室里。这样一个化学系的本科生,甚至还经常在外尔出差时帮他给数学系的本科生代课。
这时,你可能又忍不住猜:他之前给了爸爸一个尚可的交代后,是不是此后就放弃了化学,完全投身于数学研究去了呢?
其实也不是。因为3年后,他成功地拿到了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化学学位,各门成绩现在还保留着档案,都是A。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数学对冯·诺伊曼的吸引力,也能体会到化学对他来说是多么没有挑战。但他没有被求知欲牵着完全倒向数学,而是依然可以按部就班的把不太感兴趣,又觉得有点麻烦的化学搞定。
经济学研究
在冯·诺伊曼的经济学研究中,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1922年暑假,他在哥廷根遇到了一个小老乡。聊天过程中,小老乡把自己在剑桥读经济学的课本给冯·诺伊曼看,一下引起了冯·诺伊曼的兴趣。他马上又找了几本经济学著作,一口气看完。这相当于在暑假集中自学了几门经济学课。
学完的感受是什么呢?冯·诺伊曼在自己的笔记中抱怨:经济学所用的术语都是模糊不清的,这让数学难以发挥作用,因为没人知道到底问题是什么。经济学的成熟度,还不如17世纪的物理学。
之后,冯·诺伊曼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经济学领域建立数学模型。但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进去,这件事在他后来22年中断断续续做着。
1928年,他建立了第一个数学模型——零和博弈中的极大极小值定理。
1929年暑假休假时,他发现著名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书中的错误,修正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1937年,他提出的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开创了后来的数理经济学。这门学问后来还成为了苏联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
1944年,他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本600多页的书。
凭借这些成果中的任意一项,冯·诺伊曼都完全可以在经济学上开立门派。但他每次对经济学的关注,都像是一个过客,一个阶段性成果出来以后就转身忙别的去了。
因为他知道,经济学中概念的模糊不清虽然有人的原因,但更多是由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决定的。在人类还没有很好的方法之前,这些复杂系统就是个泥潭,一脚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所以在有彻底解决方案之前,即便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声望,也不值得全身心投入其中。
计算机研究
冯·诺伊曼最广为人知的对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发明,也体现了这一点。
广为人知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其实并不是冯·诺伊曼设计的。冯·诺伊曼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ENIAC已经基本设计完毕了。他作为顾问加入后的任务其实是升级改造它,而其中最大的改进部分就是指令的存储环节。
那个年代每一步的改进,都是今天所有计算机的基石。ENIAC团队的工程师和作为顾问的冯·诺伊曼都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之后的行为模式却很不一样。
比如团队中的核心人物莫奇利和艾克特,就把这些进展当作是和蒸汽机、无线电、电话一样的伟大发明。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赶紧注册专利,成立公司,把想法产品化,然后在交易所上市。
但冯·诺伊曼的预感是,当时的计算机还很原始,要设计出更加通用的计算机,还有相当多的改进工作要做。如果在当前的起步阶段就通过注册专利设置障碍,不利于这种前途远大的机器在今后的发展。
所以他的做法是和ENIAC团队的负责人戈德斯坦(Herman Goldstine)一起,把改进ENIAC过程中的思路和通信内容,整合成一份完整的资料出版了。他希望这些知识尽快为外人所知,让其他潜在的天才和当前这些打算封闭消息、自己创业致富的人达成充分竞争。这份报告就是计算机史上著名的《101页报告》。
等报告出版后,冯·诺伊曼的注意力又一次离开了这个行业。他没有被史上最有潜力的创富机会诱惑到,也没有着迷于计算机体系设计中的那些细节。
是的,在那个年代确实还有另外一个小伙子,沉迷在计算机数学基础的细节研究中不能自拔。他就是我们曾经在《密码学30讲》第26讲说到的图灵。
为什么冯·诺伊曼能跨领域高产?
可以说,冯·诺伊曼之所以能在研究领域上涉猎这么广泛,和他从不被一些执着的欲望控制住有关系。
任何领域都是越往深处走越难,就算智力、体力维持不变,工作强度也维持不变,对一个人来说,出产的成果也一定是越来越少的。
但冯·诺伊曼和所有领域都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一个出色的成果完成后就转身忙别的去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他抛去其他所有的选择。也许从小的贵族经历让他有了一个比别人更宽的视野,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一惊一乍,也很难有什么东西会让他完全不能接受。
这样的行为习惯让他总能被一些机构迫切的需求推着走。而那些迫切的需求背后,往往就是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些好问题已经有人帮他选出来了,所以他只要挨个解决,效果自然就超级好。
下节预告
接下来四讲,我会详细说一下冯·诺伊曼在各个领域的科学成就。第一个要说的,自然是人们提到冯·诺伊曼时最常说一个词——“计算机之父”。
我是卓克,咱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