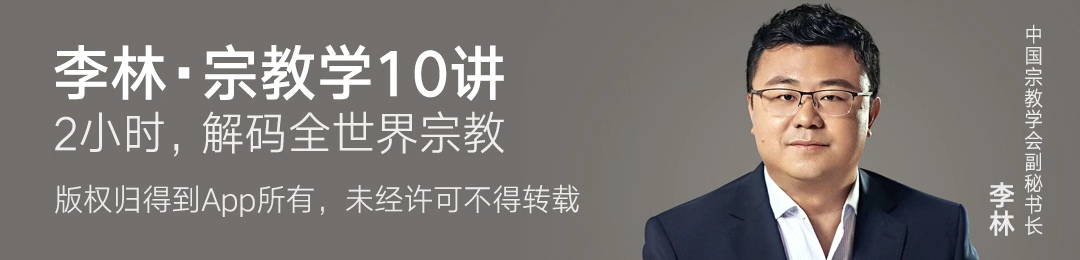你好,我是李林,欢迎来到宗教学10讲。
上一讲我们说到,宗教是一个独特的意义生产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我把它叫做“超余”。宗教中设定的超余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基督教里的“上帝”,再比如佛教里面的“涅槃境界”。
从宗教学的视角看,宗教活动就是人以信徒的身份和超余打交道,在自己与超余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所有具体的宗教活动,都是围绕这个关系展开。世界上的宗教千姿百态,但在我看来,从信徒对待超余的不同方式看,宗教现象都可以归结成两大基本模式:一类我们称为“人-神模式”,是另一类我们称为“人-人模式”。在人-神模式当中,信徒是以无条件信赖“神明”的方式和超余相处,在“人-人模式”当中,信徒更多地是以一种人与人之间玩利益交换的方式对待超余。
“信仰”模式的意义生产十分稳定
这一讲我们先来讲“人-神模式”。在“人-神模式”中,信徒对待超余的方式,我们通常叫做“信仰”。宗教中的“信仰”是一种不需要理由的相信:不论缘由、不计得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选择相信自己的宗教。
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约伯记》,讲到了“信仰”的问题。约伯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幸福,生活富裕。他的事迹被撒旦所知晓,撒旦对上帝发出挑战,他说约伯之所以虔诚,只不过是因为获得了物质上的利益;只要剥夺掉这些物质利益,约伯自然会舍弃他的忠诚。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于是,撒旦让约伯遭遇了接连不断的打击:先是损失了财产,然后又失去了子女,最后身患重病,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说,你还坚持信仰做什么呢,你放弃算了。但约伯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有意义的,没有丝毫动摇。后来,约伯成为了基督教中“信仰坚定”的代表人物。
你看,这种对信仰的要求实在很苛刻。要是只在宗教故事中讲一讲也就罢了,可这种要求甚至延伸到了现实中,是不是好像有点不讲道理呢?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信徒,不论你遭遇了怎样极端的困境,你的神,或者我们说的超余也不会现身,替你解决问题;无论你多么虔诚,信仰也不能改变你面临的客观状况。然而,它却要求你坚持无条件地相信它。我们肯定要问了,宗教凭什么这样要求呢?
我先把答案交给你:原因在于,宗教原本就不处理客观世界中的物质问题,它最大的功能是给人提供意义。人不同于动物,总是会自发地寻求意义。宗教只要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就能得到信徒的认可。而且宗教也确实很充分地做到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意义生产机制,宗教能够全方位地覆盖从日常生活到极端情形下的意义供给。在“人-神模式”中,这种意义供给十分稳定。
日常生活的意义
我给你举三个例子,来看一看“人-神模式”中的信仰,是如何全方位地给信徒提供了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看犹太教的安息日传统,这个传统给日常生活赋予了神圣性,让平凡的生活获得了意义。在犹太教传统里,每周五的日落之后到周六的日落之前,这一整天的时间中信徒都不能劳作。根据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的内容,甚至连做饭都不行,因为家务劳动也是劳作,只能提前准备好食物。到了现代,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在安息日甚至不能开灯关灯,打电话、开车、出远门也是禁止事项,娱乐活动更不用说了。
旁人看这件事可能会觉得不解,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安息日的规定来源于犹太教信仰中的创世论: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信徒守安息日,实际上是在纪念上帝创造世界。在安息日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么要做的是什么?是休息和敬拜上帝。通过安息日,信徒与上帝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之前六天的辛苦工作也不简单了,那是为了给安息日敬拜上帝做准备。日常生活就这样被赋予了一层神圣的意义,而不只是繁杂琐事、柴米油盐。
工作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它给工作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在清教徒看来,工作是一件和人生终极目标有关的事情。
人生不只是“生下来、活下去”,谁也不愿意碌碌无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普通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呢?是生活所迫吗,或者是为了赚钱享受?清教徒认为,都不是,工作具有更加神圣的意义:勤奋工作是上帝选民的印记。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要说到清教信仰的特点。清教是从基督教新教里的加尔文宗发展出来的,这一派的特点是相信预定论。意思是,一个人会不会被上帝选中、获得救赎,早就注定好了,和这个人的行为没有关系,一切都看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增加获得救赎的概率。问题来了,既然如此,清教徒为什么还要选择勤奋工作呢?
答案是,因为勤奋工作并不是得救的“理由”,而是得救的“标志”。清教徒认为,被上帝选中的人,他在俗世的目标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增加上帝的荣耀。对工作认真负责,远离世俗的享乐,就是这一类人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勤奋工作不会让你被选中,但一个注定被上帝选中的人,在生活中一定会勤奋工作。清教徒选择勤奋工作,不是因为拜金,也不是为了赚钱享乐,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一来,平凡的工作,就和人的终极追求发生了关联,获得了更深刻的意义。
苦难的意义
最后,宗教还能为苦难赋予意义,让人在最极端的困境中,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撑。我们来看一看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故事。
在1943年的纳粹德国,朋霍费尔因为从事地下反纳粹活动被关进了特别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面对被囚禁的生活和死亡威胁,朋霍费尔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承受苦难的人能够比平常人更了解信仰的真谛。
在这位神学家看来,承受苦难同样是培育和表达自身信仰的一种方式。因为在基督教中,痛苦和苦难有着独特的意义:耶稣就曾经为了全人类而受难。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主动地去承担责任、经受痛苦的考验——这一切让他更加接近基督,拉近了与上帝之间的距离。对于这位神学家来说,苦难不仅没有动摇他、摧毁他,反而让他更深地理解了自己的信仰。无意义的苦难,就变成了有意义的经历。
你看,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到最极端的艰难困苦,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意义,这和物质上的得失可是两回事。犹太人守安息日,让日常生活获得了神圣的意义。清教徒勤奋工作,是把“勤奋工作”看作是上帝选民的印记。神学家在死亡和苦难面前坚持信仰,并不是认为信仰能够消除现实的苦难,而是要通过信仰,找到苦难的意义。
“不讲道理”有道理
在宗教内部看,不计得失的信仰,更多地是体现出个人的虔诚。但从宗教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信仰“不计得失”,其实是让意义的获取变得稳定。
这种稳定对于信徒来说特别重要。团体需要稳定的共同意义来搭建共识,个人需要从稳定的意义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感和精神支持。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信徒在信仰面前计较得失,他选择相信某个宗教,不过就是为了换取某种个人利益,他和超余的关系就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利益消失,就没有理由再坚持信仰,从信仰中产生的意义也随之消散。那么,前面说到的那些个人的精神支持、团体的共识就会失去基础,带来从个体到群体各个层面的动摇和混乱。
“不计得失”的信仰,看上去不讲道理;但恰恰是因为不讲道理,不去计算利益得失,才让“相信”这件事不会随着利益得失的改变而改变,让意义的供给能够保持稳定性。
好,人神模式,也就是信仰模式,我已经给你讲完了。讲到这里,你也许已经想到,在生活中,其实还有一些宗教行为,并不是那么的“不计得失”。这就是宗教关系的另一种模式,“人-人模式”。下一讲,我们继续。
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无条件地相信某个事物”或者“不计得失地去做某件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