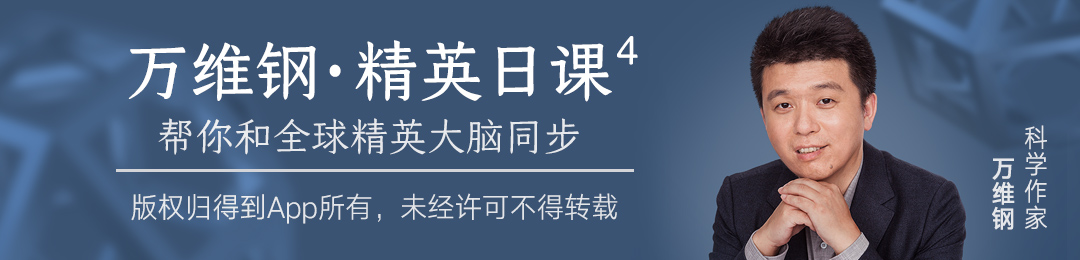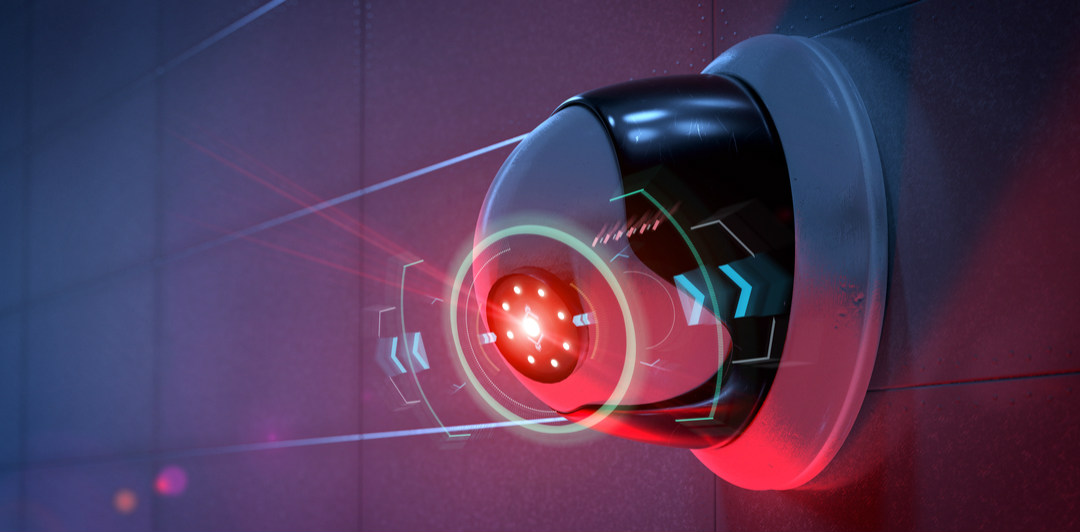来自日课:系统问题,系统解决
"系统解决问题会面临很多跨部门沟通协调问题,我认为不是所有事件都能系统解决,万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事情可以不解决比解决成本更低呢?"
"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先判断这是一个系统问题还是一个个体问题呢?"
是的,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几年前有一本由几个实干的创业者写的小书很流行,叫 Rework,中文版叫《重来》。这本书中有一些创办公司、推出产品和管理公司的经验之谈,说的都很实在。
这本书中有个思想,就是没有必要一听说有人犯了错,就在全公司制定一个相应的政策。比如你们公司有个员工,跟客户一言不合动手,还把客户给打伤送医院了,媒体报道,舆论哗然。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责成相关领导作出深刻检查,然后对《员工守则》进行修正,以期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呢?
Rework 这本书说,真没必要。像这种事情本来就很少出现。你专门为此修改系统,反而让它成了公司的一个永久伤疤。乱七八糟的规定一大堆,人们会不知所措,整个公司会丧失活力。正确的办法是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然后就完了。
很多错误都是就很少出现的,很多事情就是无缘无故地发生了。可能当时觉得挺闹腾,事后就无声无息了,没必要反应过度。
我们需要在乎的是那些趋势性的、规律性的、可能影响系统走向的事件。而解决方法最好是柔性的。就像冰岛解决中学生抽烟喝酒问题一样,润物细无声,不要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解决”。否则就可能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带来一大堆大问题。
来自日课:支点和预警
"当假警报多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让人选择性地忽视从而达不到真正想要的预警效果呢?怎么衡量“收益和成本”问题?有哪些办法,能够延缓或者减轻假警报可能造成的影响?"
假警报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比如现在汽车都有个报警系统,非正常打开车门、或者车被碰了一下就会嘟嘟嘟地猛叫,这个设计的本意是防止有人偷车,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操作不当导致的假警报。
那你说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报警功能呢?也不一定。报警功能可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把偷车变成了一个技术活,也许能防止车被偷,这是一个上游功能,它起作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其实汽车这个还算好的。希思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事儿。有人对五个医院的 ICU 跟踪观察了一个月,其中一共有 461 个病人。医院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时刻监控病人的状况,一旦有哪个指标不对就会发出警报。那你说,这些病人一个月中一共发出了多少次警报呢?
答案是250万次!你可想而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假警报。而且有这么多警报就等于没有警报,医生们会产生“警报疲劳”,他们会变得不再敏感,会直接忽略警报。所以医院也想了办法来控制警报,比如一个办法是把大多数警报设置成文字式的 —— 只在屏幕上显示,你不看也就算了 —— 然后只把其中那些特别重要的指标发出的警报设置成声音的,逼着你必须注意。那你说,这一个月中的声音警报有多少条呢?
答案是 40万条。相当于平均每个病人、每天发出 187 条声音警报。这就是 ICU 医生的日常。你能想象,其中必然仍然有大量的假警报,但是现在医院能做到的也许就只有这样了。没有什么好算法能再进一步减少假警报了。
所有测量都是不完美的。就拿新冠病毒的测试盒来说,有 95%准确率就算是好的了。而剩下的那 5%的出错率,你希望它出假警报 —— 也就是“假阳性”:把一个明明没有被感染的人说成是病毒携带者,你宁可冤枉他。因为如果是“假阴性” —— 这个人明明被感染了而你没测出来,那危害就太大了。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宁可多一点假阳性,也别产生假阴性,我们就不得不把报警器、或者测试盒的敏感度,调的比真实情况高一点。你不想要“尽可能准确的判断”,你想要“尽可能保险的判断”。所以你得到的假警报数其实比技术的实际监测能力还要多一些,但是你认了!这是你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来自日课:官僚系统的悖论
"信息技术的普及有可能改善官僚系统的悖论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按理说,信息越完整,人们做事越明白,应该是好事,但是对官僚系统来说,有时候信息完整反而不好。咱们举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在此我推荐一本书,郭建龙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这是一本十分精彩的书,值得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读,我们要说的这个例子就来自此书。
古代中国政府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收税技术不行。理想的税收体系应该是所有人都交税,穷人少交,富人多交,就像现在这样。古代的情况却是贵族不交税、老百姓有各种办法逃税。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能逃税,一方面是官僚系统腐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府掌握的信息不足,根本不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
这个局面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包括唐朝李世民这样的盛世也是如此,动不动就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根本不给你提供税收。政府不压榨百姓,就没钱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压榨百姓,百姓不堪重负就只好逃亡,结果土地没人种,更收不上税来。
中央帝国政府为了得到收入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咱们就不细说了,这里只说一点。中国历朝历代都搞不清自己的土地和人口,但是隋朝却是一个例外。
隋文帝杨坚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在全国搞了一次土地和人口普查,并且建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户籍制度。隋朝政府能够控制社会的所有角落。逃税,在隋朝是不可能的。
对政府来说这是大好事,隋文帝有足够多的钱,做了很多很多大事。他每次大兴土木或者打完仗回来一看,仓库里的钱还是满满的。甚至到隋炀帝杨广时期,做了太多不该做的“大事”、白白消耗了无数人力物力之后,政府还是那么有钱。而杨坚和杨广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的是,民间被压榨过度,早就不堪重负了。
所以有时候政府太厉害不是好事,政府糊涂一点反而对老百姓有利。唐朝统计上来的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这使得唐朝百姓的实际税负只有隋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唐朝藏富于民,这才有了贞观之治。郭建龙说,“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
后世的皇帝吸取这个教训,有时候宁可让自己的政府效率低一点。比如说据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在《盛世·康乾》这本书中介绍,康熙皇帝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负担,就经常反对地方官员去彻查土地。四川省开垦了很多荒地,康熙专门阻止四川总督年羹尧丈量土地。清朝立国五十多年之后人口统计已经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了,农民常常是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人缴纳丁银,康熙也不管。因为康熙知道,一旦官僚集团有了更高的征税能力,必定是中饱私囊,中央政府得到的好处会很少,而老百姓吃的亏会很大。
所以信息不见得越发达越好。当然,如果是双向的信息,让老百姓也了解政府在哪里花钱、大家一起算算国家到底需要多少钱,该加税加税、该减税还能减税,那可能是信息越发达越好。
来自日课:摸着石头过河
"该如何识别出正反馈和既得利益者的噪音反馈?对这些噪音反馈又该如何应对?"
世界上没有多少像快餐店给垃圾桶加个盖这样的“帕累托改进”,一般的改革总会伤害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会遭遇反对的声音。一有人反对就不改革肯定不对,对反对声音置之不理也不对,那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呢?
很难把握。咱们还是拿中国历史举例。北宋庆历年间,宋仁宗痛感朝廷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拿不出钱来,同意范仲淹搞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思路是国家财政养了太多光拿钱不做事的人,包括官员和士兵,应该把这些人裁撤掉。这个思路完全没毛病,范仲淹做事也很稳当,但是刚一执行就受到了官僚集团的抵制。而仁宗皇帝的性格又很软弱,庆历新政才弄了一年就不了了之。范仲淹也没脾气,只写了一篇《岳阳楼记》聊以表达情绪。
但是国家没钱还是不行啊。仁宗去世后,到了宋神宗年间,不但打仗没钱,连发生自然灾害救灾的钱都拿不出来了。那既然范仲淹节流的思路失败了,宋神宗就采纳了王安石开源的思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使用各种手段给政府捞钱。
王安石变法也是一出台就受到了反对,特别是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富弼、苏轼这些当时公认的优秀人物都反对。但是王安石和宋神宗的意志非常坚决。好人不支持,王安石就用了很多投机钻营的人推行变法。变法遭到民间抗议,王安石也能承受。人说王安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也不在乎。
变法真的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是变法带来了很多二级效应。对民间经济的破坏就不说了,对政治局面的破坏是朝廷上从此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党争,大臣们只知道斗争没有人做实事。范仲淹那种稳稳当当做事的人、苏轼那样就事论事的人,都再也无法生存了……
那我们现在看来,范仲淹改革的错误在于推行不够狠,王安石的错误在于太狠。其实神宗年间的内外局面并不算太坏,王安石的很多政策都挺好的,完全可以慢慢推进。结果王安石彻底毁坏了北宋官僚体系,能办实事的好官都没有了。等到后来金人崛起、危险迫近、应该激进改革的时候,已经没人能推动任何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