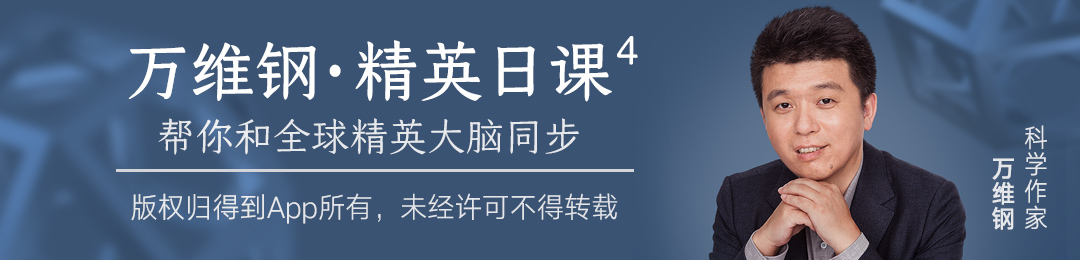咱们继续讲雨果·梅西尔的《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梅西尔否定了“乌合之众”的说法,认为大规模的人群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影响,这是一个不一般的立场。
我们专栏讲过这方面的话题。我们讲过斯科特·亚当斯的《以大制胜》,总结过特朗普“武器级的说服力”;讲过吴修铭的《注意力商人》,总结过现代媒体是如何影响人的。当然还有赫拉利的《未来简史》,赫拉利特别担心的就是,如果人工智能特别厉害,就可以通过定制信息的方法来精确地影响每个人的政治立场……这不就把人变成可以随意摆弄的绵羊了吗?更何况,你肯定还听过传播学、广告学等各种理论,说的都是人群是可以影响的。
影响是肯定能影响的,但是能影响到多大程度,怎么个影响法,这个不一定。读了梅西尔这本书中的各种研究结果之后,我现在相信,赫拉利对未来的担心,是多余的。
1.纳粹的宣传有用吗?
希特勒,可以说是现代宣传事业的创始人。他发明了用公开的激情演讲来煽动民众这个做法,首创了到各地做巡回演讲去竞选拉票。早在监狱里,希特勒就悟出来了收音机的威力,他设想了用收音机做大规模宣传,他要向全国人民不断地、重复地播出政治信息,让每个人都听到。
正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希特勒掌权之后,纳粹宣传负责人戈培尔,把这套思想不折不扣地执行了。那这个方法管用吗?
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重新研究了德国的宣传效果。纳粹最大的宣传主题是反对犹太人。咱们可以考察一下1920年代到193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他们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正好是年轻人,最容易受宣传影响。相比其他年代出生的德国人,这批人对犹太人的反感情绪,的确高出了5%-10%。这么看的话,纳粹的宣传的确有用。
但是你还得看更细致的数据。当时收音机还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在德国全国普及。如果宣传有效,那按理说,应该越是收音机覆盖率高的地方,人们越反对犹太人,对吧?但统计结果却是收音机的覆盖情况和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并没有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呢?是希特勒上台之前人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本来就反感犹太人的人,听了宣传会更加理直气壮地仇视犹太人,政府宣传相当于是给了个官方许可;而本来不反感犹太人的那批人,听了官方宣传反而还容易产生逆反心理。收音机其实没啥用。
咱们再看另一个议题。纳粹有个理念是要把全国的残疾人都给安乐死,也是大肆宣传,但是被全国人民都给抵制了,啥作用也没起。纳粹呼吁全体国民都要为战争机器贡献力量,德国老百姓也给来了个阳奉阴违。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根本做不到让德国人衷心热爱纳粹党。德军明明打了败仗,戈培尔非要说打了胜仗;纳粹官员明明很腐败,戈培尔非说是好官,结果是大家干脆都不信广播,宣传被人们忽略了。
那你说纳粹士兵作战很勇敢,这总是宣传的作用吧?底层士兵的确没有因为和平理念而拒绝作战,但是他们也不是因为支持纳粹的理念而勇敢作战的。新的研究认为,士兵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小团体而战,是为队友而战。真到了战场上,首先是战友情,其次是对战败的恐惧,纳粹洗脑的影响不大。
宣传,并不能给人灌输什么新理念。宣传能做的只是再次确认人们之前就有的价值观、共识和偏见。
如果宣传不能驱动人群,那什么才能驱动人群呢?
2.造势和乘势
很多人认为领袖人物都是鼓动者,能“造势” —— 其实那些真正调动了大规模人群的人,是在“乘势”。
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学科。老一辈历史学家距离历史是更近,但是不一定就能看明白。新一代历史学家离得远了,反而更容易有一个更客观的视角、更超脱的看法,更能使用科学的方法不偏不倚地去分析当时的情况。
梅西尔总结了几本新历史书的观点,认为不管是那个著名民意操纵者、古希腊政客克里昂,还是希特勒,这些人都并不是*引导*了民意,而只是*代表*了民意而已。
希特勒是怎么上位的?并不是他煽动了德国人的情绪,而是当时德国那个政治经济状况,导致人们的极右思想就是很强大。希特勒只不过是善于倾听民意,乘势而起。老百姓们都这么想,没人带头、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把它说出来也成不了事。乘势者代表了民意,就可能把人组织起来。
其实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所谓个人魅力并没有什么盲目崇拜。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完全和德国的经济状况和军事状况挂钩。经济形势好、一直打胜仗,希特勒的声望就提高。等到希特勒把全国都卷入战争机器,战争影响到了每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的声望就下降。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战败,希特勒的声望直线下降。
再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南非科萨部落的故事。有一位女先知说,我们把牛杀了,牛会变成鬼军和英国人作战;只要你们听我的,将来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我们吃的用的要啥有啥,连残疾人的病都能治好……人们就真信了,真的杀死了好几千头牛。
这些的确是事实,但是事实背后还有四个细节。第一,当时正好赶上一种大规模的流行疾病,许多牛得病,不杀也得死。第二,科萨人的确有杀牛祭祀的传统。第三,科萨人的经济状况很不平等,大部分牛都掌握在贵族手里。第四,当时正好赶上了自然灾害,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快过不下去了。
按理说,这时候贵族应该把牛分给穷人吃,但他们不但没这么做,反而把牛卖给英国人赚钱。那么现在先知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借口,人们当然就蜂拥而上把牛给杀了。并没有人主动去杀自己家里没得病的牛。
如果先知靠的是紧急状况,那宗教又是如何长期传播的呢?答案是……用今天的话来说,靠“地推”。
隔着历史看,基督教好像一下子就起来了,但实际上基督教的传播速度很慢。从公元40年到公元350年,整整310年内,基督教从1000个信徒发展到了3400万个信徒 —— 这个速度仅仅相当于每年有3.5%的增长率而已。
人们为什么去信教?并不是像病毒那样听神父一讲就被感染了。大多数人坚持长期去教堂,是因为在教会中找到了社区感,大家经常互助,感觉挺温暖。
现在摩门教传播也是如此,都是依靠亲戚朋友之间,今天我介绍你下礼拜你拉上你妹夫,一点点地推动。而就是这样,绝大多数人也是去过一次教堂就再也不去了。一个教徒一生之中,也就能拉来几个人而已。
信仰这个东西也许对知识分子能管用,对老百姓的作用其实是很小的。天主教会在最强盛的时候,都不能用信仰说服百姓们好好纳税。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糊弄教会。
事实是精英们的确在卖力宣传,是真想让人相信,但是人们真不信你也没办法。
3.广告有用吗?
我们的生活中铺天盖地都是广告,但你要说广告到底有没有用,这还真不好说。包括一般商品的广告和政治竞选的广告,梅西尔调研了很多研究结果,我给你总结一下。
广告有两个可能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告知,是让没听说过这个产品、不知道你是谁的人了解你。第二个作用是好感,是让已经知道这个东西的人,改善对这个东西的印象。
梅西尔这本书的结论是,第一个作用很明显,第二个作用几乎没有。
比如你作为一个政客想要竞选总统,老百姓得认识你才行。你属于哪个党,你的政策理念是什么,这些你得告诉大家。至于你对一个具体议题的看法,如果我之前并不关心这个议题或者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我可能会因为信任你,而接受你的看法。
新产品的确需要做广告。罗胖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说淘宝,我们以为早就尽人皆知了,可是在春晚做了广告,服务器马上就爆了。之前是城里人知道淘宝,但农村地区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春晚广告确实很有效。
要这么说的话媒体报道应该更有效。但是如果媒体不报道你,或者报道你了别人没收到,你还是得花钱做广告,这没问题。
而如果人们已经都很熟悉你了,比如大家都知道希拉里是谁,她再想用广告提升自己抹黑对手,这个真没啥用。竞选需要花钱,但不是谁的钱多谁能当选。再比如说我已经喝过这个啤酒了,那好喝就是好喝不好喝就是不好喝,你再怎么做广告都对我无效。
这两个道理听着很简单,但是以前人们真不知道。是最近几年有人花巨资做了大规模的随机实验才知道。
你花钱做了广告,然后这个选区的民意反转了,这是广告的作用吗?真不一定。可能以前人们不了解你,可能人们不愿意公开支持你。光有数字不行,得做实验才行。
而且有些广告公司会拿一些新颖的名词忽悠客户。前一阵有个丑闻,说一家私人的政治咨询公司,叫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号称能根据 Facebook 的用户数据,通过定向投放信息,精确影响人们对某个候选人的态度……而事实上这已经被证伪了。那个公司最多也就能影响几千人,实际作用几乎为0。
再比如说,我分析一下微信用户都发什么朋友圈,给他们来个精准定向广告投放,这有用吗?有人做过研究,相对于比如随机投放,这种定向广告真能给你增加的购买人数,在几百万人之中也就几十个人而已。
那明星做广告有用吗?你要能说服张文宏给一个药代言,那绝对有用,因为人们认可他的专业水平。但如果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专家,比如你让鹿晗代言一个咖啡,相对于没有明星代言,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对品牌形象有额外的正面影响。
人们总是混淆广告的第一种作用和第二种作用,把知名度等同于好感度。
归根结底,人是开放而又机警的。你可以轻易说服一个人尼罗河有多长,但是你很难说服他改变宗教信仰。一对一交谈可以摆事实讲道理;读书上网课可以花时间琢磨,但你要说大规模宣传和广告,同时对一大群人说话,你就只能寻求这些人的最大公约数,想要说服他们接受和自身观念相反的东西实在太难了。
简单说,你再懂宣传,也不可能忽悠一大群人去做蠢事 —— 除非他们认为别的选项是更蠢的事。
那既然人们如此理性,为什么还有人真的相信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呢?咱们后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