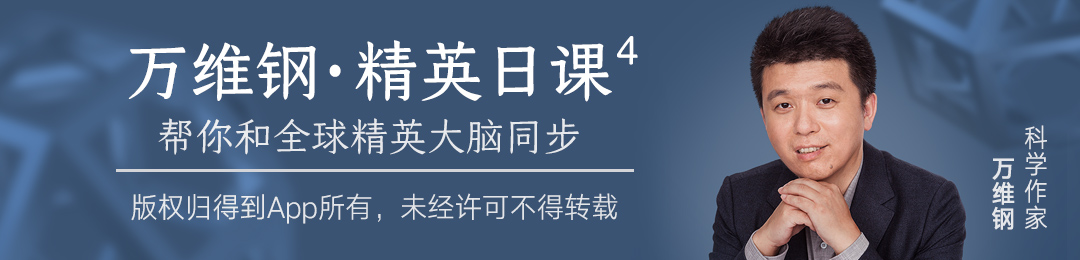上一讲我们说了两个保持机警的手段,一个是如何接受新信息,一个是听谁的。这一讲的主题是另外两个手段,一个是我们如何决定是否相信一个人,一个是我们如何对情绪做出反应。
辩论继续进行……
A:我们先说说如何识别谎言吧。你说人是机警的,但据我所知,人非常不善于识别谎言。比如以前很多人相信保罗·艾克曼的“微表情”理论,说有些专家可以通过一套微表情来识别谎言,但是这个理论现在已经被学界抛弃了 [1]。
B:是的,微表情的确不靠谱。不但微表情不靠谱,最近还有人把之前的几十项研究综合在一起做了个荟萃分析 [2],结果进一步证明,所有的身体线索 —— 不管是什么肢体语言、眼神接触之类 —— 统统都不靠谱。没有任何专家能找出可靠的说谎特征规律来。
A:难道我们就无法识别谎言了吗?
B:的确不行,而且这符合演化思维。你想想,如果真的有一个特征能识别谎言,说人只要一说谎就会如何如何,那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这个特征肯定已经被我们发现了。那人还怎么说谎呢?说谎者肯定就会避免表现这个特征!
A:所以这样的特征就不可能长期存在……演化思维还真管用。这让我想起了博弈论……
B:这其实就是博弈论说的“混合策略” [3]。你不能总用同样的方式说谎,必须随机选择说谎的表情,谎言才可能有用。
A:格拉德威尔在《与陌生人交谈》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蒂姆·莱文的“默认真话理论” [4],说我们总是轻信别人的话。我看这些证据都不利于你的论点啊,我们不能识别谎言,又何谈“机警”呢?
B:我们很难识别谎言,但是我们有办法抑制说谎。“默认真话理论”不是绝对的,我们对小事儿可能无所谓,真正面对利益攸关的事儿没有那么容易被骗。如果骗人如此容易,那老实人必定一天到晚吃亏,发展到最后肯定变成大家都谁也不信,干脆谁的话都不听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这样的。
A:又是演化思维。那你说,如果你都不能发现谁在说谎,怎么抑制说谎呢?
B:游戏的真正玩法不是要发现说谎者,而是要发现说真话的人。任何人说一句话,你都可以先假设他说的是谎话 —— 他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你才可以相信他。
A:这听起来很像“谁主张、谁举证”。一句话是否可信,不是由听话的人决定,而是由说话的人决定。
B:非常正确。这句话是谁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都很重要。其实我们有机制能确定这个人说的是真话。最关键的就是,如果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激励*(incentive),比如是合作关系,交流是为了一起把事情做好,那就不会互相欺骗。
A:在这种情况下说谎对谁都没好处。可是生活中,绝对一致的利益关系恐怕不存在吧?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连母亲和她肚子里的婴儿之间都存在利益冲突。如果我们判断在这件事儿上有利益冲突,有什么办法确保对方说真话呢?
B:办法就是惩罚。谁说谎话,我们就惩罚谁。
A:这可不一定。比如你网购了一双鞋,商家说质量特别好,结果你穿了几天就坏了。可是你犯得上为了这点小事,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告他吗?惩罚他对你没好处。
B:告他对我的确是得不偿失。但是我可以在网上给他一个差评,我可以损害他的声望。声望是社会对说谎者最大的约束。不管我的力量多弱小,我都可以发起对一个人声望的挑战。而且人们也乐意传播扩散这种坏人坏事。你看不管是什么社会,平时大家闲聊都爱说些谁谁谁的坏话,这就是声望机制。
A:要这么说的话,声望还不只跟说谎有关系。比如这个商家虽然不是故意骗我,但是他的服务没有尽心尽力,那他的声望也应该受到损害。
B:你说的这个就是“尽责性(diligence)”。一个人有水平但是不尽责,和这个人没水平、和他有水平但是骗我,这三种情况其实对我来说差别不大。所以要想真正取得我们的信任,这个人必须是尽责的才行,信任测试本质上是尽责测试。
A:我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声望系统这么重要,会不会把人给逼的对所有事情都特别尽责?那岂不是把好人给累坏了吗?
B:人是很聪明的,为了取得别人的信任,除了激励和尽责,你还需要管理他人对自己的预期。比如人家拜托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打算全力以赴把这件事做好、而且确实有把握做好,你可以说“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如果你不打算投入特别大的精力去做这件事,你可以说“我尽量帮你办”。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把握,只想尝试一下,你可以说“我试试”。你“承诺(commitment)”的等级可以不一样。
A:如果一个人的承诺本来就很低,最后就算事情没办成,他的声望也不会受到损害。
B:是的。我们有很多实验能够证明这一点。两个人都承诺要做一件事,最后都没做成,那个之前给了信誓旦旦的承诺的人的声望下降了,而那个之前就说的很谦虚的人的声望不受影响。
A: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给一个谦虚的承诺呢?
B:因为不谦虚的承诺更有可能帮你拿下订单。承诺是声望的一部分,承诺能让交流更有效。
A:激励、声望、承诺,确实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机制。但如果一个人跟我没有什么共同利益,社区又不是很关心这个人的声望,他是不是就可以撒谎了?
B:这种情况下该着急的不是你而是他:你根本就不相信他。这个人等于是没有在社会立足,他需要一个个人品牌。这就是为什么陌生人的互动都是比较保守的。信任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本。现在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很多事情都不好办。
A:所以我们对别人的信任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B:这就叫机警。很不幸,信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瓶颈。
机警的第三个手段是信任。下面进入第四个手段:“情绪”。
A:有个词叫“乌合之众”,一群人聚在一起情绪互相感染,就容易做傻事。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一大群人走上街头,打砸抢烧,做了很多坏事,这也叫机警吗?
B:咱们先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20世纪以前的学者的确相信乌合之众这个说法。但是现在早就有了更好的研究。乔治·雷德(George Rudé)1959年有本书叫《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说大革命期间群众并没有搞很多暴力,人们都很克制,大部分抗议是和平的。的确有一些人被屠杀了,但大多数都是政治犯,并没有没有多少无辜的路人被杀。群众一边游行,街头还有小摊小贩在贩卖商品!你再比如说,有人研究了十九世纪末2700起大罢工事件,发现其中只有不到100起涉及到暴力,而所有这些暴力事件加在一起,一共才死了1个人。
A:可是你不能否认,疯狂是可以传染的,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如果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地笑了,其他人也会跟着笑,甚至历史上有时候这种怪异的笑还能持续好几天,这又如何解释?
B:咱们还是用演化思维。如果情绪这么容易传染,一个人疯狂了其他人就会都跟着疯狂,那人群岂不是太容易被人摆弄了吗?这样的群体怎么可能存活到今天呢?
A:可我们就是会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别人愤怒我们也会愤怒,别人恐慌我们也会恐慌,别人悲伤或者高兴,我们也会跟着悲伤或者高兴。如果情绪对其他人毫无影响,那情绪这种东西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不也是演化思维吗?
B:你说的很有道理,情绪确实是一种比较可靠的信号。之所以可靠是因为情绪是自发的,你愤怒也好悲伤也好,很难假装。看到别人的情绪,我们也会跟着产生情绪,这个基本上是自发的,不受控制。
A:既然是自发的,你为什么又说我们不会被别人的情绪所传染呢?
B:我们必须得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自发(automatic)”,一个是“强制(mandatory)”。你看见别人笑,你也会跟着笑,这个是自发的,是你无意识的反应。就好像你看到蛋糕想吃一样,你可能都控制不了自己流口水。但是这个反应不是强制的。
A:都控制不了了怎么还不是强制的呢?难道你看见蛋糕不想吃吗?
B:如果我之前刚刚吃了很多蛋糕,都已经吃撑了,我看到这块蛋糕就不但不想吃,还感到恶心。恶心,也是自发的情绪。你看,蛋糕可能让我产生两种不同的情绪,虽然都是自发的,但它们不是强制的。强制是什么呢?是只能有那么一个反应。比如医生拿小锤子在你的膝盖上敲一下,你会有膝跳反应,这就是强制的。
A: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别人的同一个情绪,会有不同的反应。
B:是的。比如你的朋友哭了,你也会跟着哭,他笑了你也跟着笑。但如果你的敌人笑了,你会跟着一起笑吗?
A:我们对别人情绪的反应,跟对方是谁有关系。
B:跟对方是谁有关系,跟我们自身的状态有关系,也跟当时的情境有关系。我们通常只会被关系亲密的人的情绪感染,陌生人疯狂不疯狂对我没影响。
A:这就回到演化思维喜欢的说法了,常见的互动都是在小团体内发生的,我们并不习惯跟大规模人群一起活动。
B:想让全国人民都和你一起哭一起笑,那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哪怕是军队都不会这么听话。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人们能一致反应,那就是从战场上逃跑!军队打败仗逃跑的时候的确是兵败如山倒,所有人都一起跑。但是这种逃跑也不是因为被害怕的情绪传染了,而是因为谁落在后面,谁就会挨打……
A:照你这么说,人的一切反应都成了理性的了!这可能吗?特朗普整天撒谎,难道美国那些选民不就是整天被骗吗?纳粹的宣传机器如果不是蒙蔽了许多德国人,怎么会有种族大屠杀呢?还有些煽动能力特别强的人,不也能调动一大群人跟着他犯傻吗?这你又如何解释?
B:嗯……这样的事情比较特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至此,关于人类如何保持机警的四个手段就都说完了,希望你得到了思辨的乐趣。至于说一大群人为什么会出现集体的怪异行为,我们下一讲再说。
注释
[1] 《与陌生人交谈》3:“微表情”靠谱吗?
[2] Hartwig, M., & Bond, C. H. (2011). “Why do lie-catchers fail? A lens model meta-analysis of human lie judgment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643–659.
[3] 博弈论11. 真正的“诡道”是随机性
[4]《与陌生人交谈》1:间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