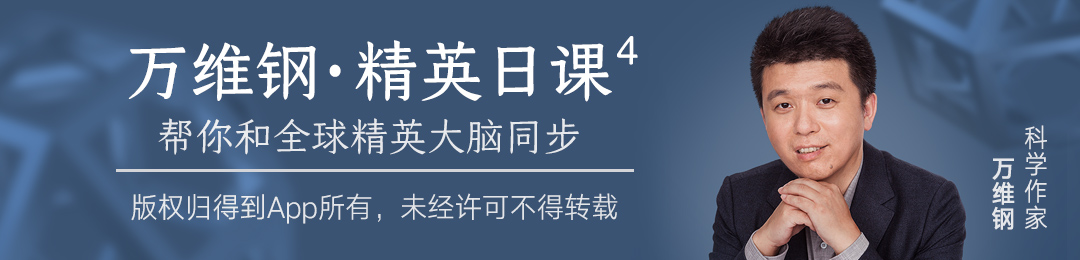我们继续讲梅西尔的《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人其实是非常理性的,没有那么容易被欺骗和煽动,而这个思想,颠覆了学界流行的观点。上一讲我们说到人的交流方式是“开放的机警”,那到底是怎么个机警法呢?这一讲咱们干脆来一场虚拟的辩论。
辩论双方,A 代表学界流行观点,B 代表梅西尔的观点。也许你会觉得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可以先别着急定论,耐心体验一场思想的碰撞。
辩论开始:
A:我认为人是比较愚蠢和非理性的,我们处理信息经常会出错。比如有个现象叫“信息茧房”,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愿意接受自己已经相信的信息。还有一个词叫“逆火效应”,说如果你告诉对方一个跟他相信的观点相反的信息,他不但不会调整自己的观点,反而会*更加*相信自己原有的观点。
B:是吗?逆火效应有那么厉害吗?
A:当然。有人做过实验,找一些共和党的支持者,这些人都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你把最新的调查结果摆在他们面前,证明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这些人反而更相信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B:你说的这个实验太老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关于逆火效应的新实验,30个受试者中只有1个人出现了逆火效应,其他的人还是根据事实调整了自己的观点。
A:一个实验不能说明问题吧?逆火效应是一个已经被多方验证过的效应。
B:你说的对,但是这里边有个关键。我们思考问题 ,一定要把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区分开。逆火效应存不存在?存在。但它说的是一个特殊情况:是这个人已经有一个强烈的政治理念的情况下,你说一个跟他这个理念相反的事实,才可能发生逆火效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跟政治理念没啥关系。比如说,你本来估计尼罗河的长度是5000公里,现在有个人告诉你,尼罗河的长度是7000公里,你会不会相信他?
A:尼罗河的事儿我不太了解,那我应该会相信他吧。
B:没错,至少你不会产生逆火效应。就拿这个尼罗河的例子来说,有实验证明,听到别人说的一个长度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己的估算往新信息的方向调整。我们平时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
A:这是不是就有点像贝叶斯定理?根据新的信息调整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理性的做法。
B:没错!其实就算不知道贝叶斯定理,人们也是这么做的。
A:但是尼罗河这个例子也不见得就能代表所有新信息。就算不涉及政治理念,人们也都是比较死板的。比如说,如果一个新信息不符合人的直觉,人们可能就会拒绝接受。
B:这样吧,我给你出道题。你可以思考几分钟再回答。请听题 ——
李明、陈涛和于丽坐在一起聊天。在某个时候,李明正好看着于丽,于丽正好看着陈涛。现在已知李明已经结婚了,陈涛是未婚的。请问,此时此刻这三个人中,有没有一个已婚的人正在看一个未婚的人?
(A) 有;(B) 没有;(C) 不确定。你选什么?
A:……应该选 C 吧,不确定。题目只说了李明和陈涛,我们不知道于丽是已婚还是未婚。
B:不对!正确答案是 A,一定有一个已婚的人在看着未婚的人。你想啊,如果于丽是未婚,那李明看于丽不就是已婚看未婚吗?如果于丽是已婚,那于丽看陈涛,不就是已婚看未婚吗?
A:对哦!这道题真有意思。
B: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A:我接受。
B:我给了你一个不符合你直觉的答案,但是你也接受了,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这个答案是讲理的,你也是讲理的。通过逻辑分析和一步步的推导,一个人是可以说服另一个人的。
A:两个理性的人辩论,最终一定会达成一致。但问题在于,没有那么多愿意跟人讲理的人。生活中就是有很多人相信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根本不听你解释。
B:其实一般人也是可以讲理的。我们的教育系统和媒体,每天都在用说理的方式传递信息。正因为讲理,人们才能逐渐接受各种不符合原来的直觉的新事物,我们的交流才越来越开放。
A: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人迷信?为什么还会有人拒绝接受一些最基本的学问?比如说,所有经济学家都说自由贸易是好事儿,可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反对自由贸易。难道自由贸易很难理解吗?
B:因为这些东西距离日常生活都比较遥远,都是一些复杂的公共事务。你得相信演化的力量,凡是跟日常生活、跟小社区比较近的事儿,演化都能让我们快速学会。国际贸易跟演化带给我们的常识有点冲突:我们总觉得如果别的国家在跟我们的贸易里赚了很多钱,那我们就一定吃亏了……这是一种古老的情绪。不过社会还是会进步的,人们慢慢地也都能接受这些思想。
A:就靠调整观念和讲理吗?可是这样的传播也太慢了,你总不能让每个人都像数学家那样做严肃推理吧?
B:的确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把所有议题都自己推理一遍,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专家的意见。
A:专家?现在谁还信专家?
说到这里,让人类机警的第一个手段已经出来了,那就是如何处理新信息。即使新信息跟我们原有的观点不符,我们通常也会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如果这个新信息是可以讲理的,我们甚至可以立即全盘接受。接下来,辩论进入下一个环节,那就是“听谁的意见”。
A:“专家”这个词,在今天简直成了贬义词。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某某专家预测的错误。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成天说经济好应该去投资股市,但股市就是没见涨。以前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不有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吗?《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这本书就说,各路专家预测的成绩,还不如让一只猴子随机做选择的成绩好。
B: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专家还是比普通人强。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你已经大半年没见过于丽了,有一天于丽的同事告诉你,于丽怀孕了。你会相信这个消息吗?
A:那我应该会相信吧。毕竟她的同事天天都能见到她。
B:这就是了。专家看过你没看过的数据和事实,你凭什么不听专家的呢?这个道理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有个实验是这样的,两个幼儿园老师,分别告诉一群三岁小孩,一个盒子里装了什么。其中一个老师当着孩子们的面看了一眼盒子,说盒子里装的是一匹小马;而另外一个老师看都没看,就说盒子里装的是一只小兔子。结果大多数孩子都选择相信看过一眼的那位老师。
A:这确实是合理的。如果有人掌握了我们不掌握的信息,他说的话的确更值得听。
B:这就是我们判断“听谁的”的第一个原则,谁有信息听谁的。第二个原则是谁有水平听谁的,我们对专家的水平也是服气的。
A:水平不好测量吧。很多成功都是因为运气好。不能说一个人炒股赚了钱就把他当做炒股专家。
B:没错!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得区分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不确定性特别强的领域里成功可能主要靠运气,但在一般情况下,水平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关于谁是最好的猎手这一点,群众心里猜测的人选和实际水平就是高度吻合的。水平很难作假,大家都看在眼里。
A:行吧!要不怎么政府有事还是应该问问专家的意见。还有别的判断原则吗?如果专家没有提供意见,或者专家的意见不统一,我们应该听谁的?
B:第三个原则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
A:多数人的意见?不是有句话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吗?
B:应该说真理偶尔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是特殊情况。你不是学过斯科特·佩奇的《模型思维》和《多样性红利》吗?这里面有个思想叫“群体的智慧”:群体判断的平均值的误差,总是是小于每个人判断误差的平均值 [1]。多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取个平均值,这个方法很有效。
A:我知道群体的智慧,可是其中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每个人的判断必须得是独立的。如果每个人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个问题,这时候把意见汇总起来取平均值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人们的判断并不是独立的,人们会互相模仿,会面临社会压力。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个判断线段长短的实验,不就有很多受试者在群体压力之下,选择了错误答案吗?
B: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说社会压力就把人给变傻了。有人事后访问了那些受试者,问他们当时为什么选错了,他们其实各有理由。有的猜测可能是自己的眼睛产生了错觉,有的以为自己是不是理解错了题意:也许题中问的是线段的宽度而不是长度?受试者并不是非要跟别人选的一样,群体压力没有那么大。
A:那另一个实验,一群人站在路边看一个窗户,路过的人就也会跟着看,这你也有什么新说法吗?
B:这个实验也有后续。如果那些路过的人跟着看是为了顺从群体压力,他们应该站在队伍的前面看,好让别人也能看见它,证明自己是个顺从者。可事实上,被测试的人通常都站在队伍后面看,别人看不到他们。这些人只是出于好奇而已,并不是想证明自己和群体一致,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
A:这三个原则,我表示可以支持。
B: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相信什么”和“该听谁说”这两个手段。因为有这样的手段,人处理信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机警的。
A:而且还有两种思维方式很重要。第一是要区分特殊情况和一般规律。第二是我们不能听说一个实验就立即接受一个结论,还应该关注实验有没有后续,最好还能采访一下受试者,看看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B:是的!你说的非常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个,也就是“演化思维”。演化思维是一把非常好用的剃刀,它能帮你直接剔除掉错误的知识。
A:有道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人这么理性,为什么还经常会被骗呢?人为什么还容易感情用事,一群人受到冲动情绪的传染,就一起去做傻事呢?
B:使用演化思维,你立即就可以看清这两个问题。
今天的对话先到这里。下一讲,两人再接着讨论“防受骗”和“群体疯狂”这两个跟机警有关的问题。
注释
[1] 《多样性红利》1:“多样性”到底好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