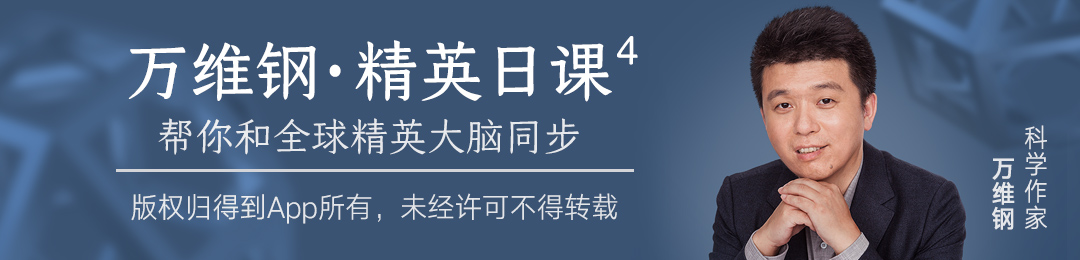这一讲的主题是交流方式的演化。我希望你从中再体会一下演化思维。
演化思维说,一个基因也好,一个性状也好,一种行为模式也好,如果这个东西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它就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不利于生存和繁衍的东西肯定不能长期稳定存在。
能让它存在的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天道”。我们专栏多次讲演化思维,演化就是生物的天道。你要想做事顺利,就得符合天道。
交流的天道是什么呢?
1.交流的难题
咱们先来说一个令人震惊的知识。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她跟肚子里的胎儿之间,除了共生合作之外,还有一场小小的战争。
这个战争是为了争夺糖。怀孕女性的胰岛素分泌水平会提高。我们知道,胰岛素的作用是把体内的糖分转化为脂肪 —— 胰岛素提高,意味着妈妈想给*自己的*身体多储备一些能量,把糖变成脂肪留下。但奇怪的是,胰岛素提高了,可是妈妈的含糖量仍然很高,就好像那些胰岛素不起作用一样,这是为啥呢?
因为胎儿分泌了一种叫做 hPL 的激素,通过胎盘传递给母亲,这个激素能对抗胰岛素。胎儿也需要糖。胎儿说你的糖别留着了,都给我吧。
妈妈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胎儿就分泌更多的 hPL。这是一场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都是恐怖平衡,各方投入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多……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么小的一个胎儿,自己还在长身体,竟然每天能分泌1-3克的 hPL!比他输入胎盘的其他所有激素高几千倍。只有战争才能让人投入这种规模的资源。
人都说母子关系是最亲密的,殊不知其中也有利益冲突。母亲不可能把一切都奉献给这一个孩子,她还有自己的人生,她还有别的孩子要照顾,她必须养好自己的身体 —— 可是胎儿只知道尽可能从母亲身上获取更多资源。
不过有冲突不等于就必须爆发战争。有冲突,又缺乏有效交流手段,才会爆发战争。
而有冲突,如果能够交流,那就对双方都有好处。
比如说,当一只瞪羚面对捕食者的时候,它可能不会马上逃跑,而是先故意在原地蹦一蹦,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在跟捕食者交流。瞪羚通过跳跃传递了一个信号:你看我能跳这么高,我的身体很健壮,你要抓肯定追不上我,干脆去找别人吧,咱俩都省点力气。而捕食者也能接受这个信号,瞪羚跳跃的高度确实反映了它的强壮,瞪羚敢冒这个险,说明这个信号是可信的。
我们专栏讲过博弈论关于发信号的理论 [1],想要让信号可信,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瞪羚的代价是冒险。有些富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去购买奢侈品,有些信徒为了证明对宗教的虔诚而斋戒,这些都是代价。
所以交流很重要,而为了让交流有效,代价很重要。讲到这里,梅西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知识。
2.更高级的交流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杰拉德・戴蒙德,三十年前出过一本书叫《第三种猩猩》,也是一本名著,我还给写过书评。这本书讲到了生物发信号的原理,讲了瞪羚,还讲到一种澳大利亚的鸟,叫花亭鸟。
雄性花亭鸟会搭建一个漂亮的屋子,要用各种花瓣、果子和五颜六色的石子装饰,好看是好看,但并没有实用价值。这些“花庭”唯一的作用是让雌鸟来评判雄鸟的能力。雌鸟觉得你这个房子装修的有水平,就可能嫁给你。

戴蒙德当时说,这就是雄鸟为了发出信号而不得不做一些无用而昂贵的事情,就好像人类中的男性买奢侈品一样……但是现在,这个知识得更新了。
新一代科学家发现,搭这个窝对于花亭鸟来说,其实并不费事,花不了多少时间也不用冒险。那这就奇怪了,花亭鸟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地吸引异性呢?因为雄鸟之间有一个协调机制。
有个科学家偶然给某个雄鸟的窝里多放了几颗蓝莓,让窝看起来更漂亮了,结果别的雄鸟看见之后立即就来把这个窝给毁了!原来其他的雄鸟认为这只鸟不配拥有这么漂亮的窝!这也就是说雄鸟跟雄鸟会互相监督:你是个什么水平,我们心里都有数,你该有什么配置就是什么配置,谁也别超标,这样大家都省力。
雄鸟通过协调,破解了那个搭窝竞赛的囚徒困境 [2]。
你看这是不是更高水平的交流:只要你能惩罚违规者,就不用发特别昂贵的信号。而我们人类,甚至可以免费交流。
3.什么人最容易被骗?
人肯定得比花亭鸟还聪明。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怎么确保可信性呢?说话实在太容易了,人们怎么识别真话假话,怎么不被骗呢?
以前主流学界认为,骗与被骗是一个能力竞赛的过程:说话的人手段越来越高,听话的人也必须越来越精明,要想不被骗,就得多思考才行。
丹尼尔·卡尼曼不是有个“系统1”和“系统2”的说法吗?系统1是直觉快速思维,系统2是理性慢速计算思维。哈佛那个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做过实验,说如果你干扰一个人的系统2,让他不能理性思考,他就会更容易相信你说的话是对的。
这些说法完全符合我们的常识。肯定是越傻的人越容易受骗上当啊,要不怎么说容易被忽悠的人群愚昧呢?
那根据这个原理,要想说服一个人,就应该让他放弃思考。有人发明了通过“潜意识”来施加影响力,比如在睡觉的时候听录音带,用观众注意不到的方式播放广告。还有人发明了“洗脑术”,也就是先对一个人进行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摧残,让他丧失思考能力,说这时候你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
但是你想到没有,我们讲过格拉德威尔的《与陌生人交谈》,我们知道严刑拷打作为一种审讯方法其实是没用的 [3]。如果放弃思考的人不会跟你合作,又怎么能被你说服呢?
梅西尔推翻了主流的说法。其实早就有研究表明,“潜意识”广告和严刑拷打洗脑术根本就没用。至于说吉尔伯特那个实验,他们给受试者判断对错的句子,答案都非常偏门,人们事先并没有成见,所以容易你说啥就是啥。更新的实验发现,如果你让受试者判断一些他本来就知道的东西,剥夺他的系统2只会让他更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
并不是越傻的人越容易被骗。而是越傻的人越保守。
4."开放的机警"
2010年,梅西尔和一些研究者重新考虑了人类交流的问题,发表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要理解这个理论,咱们先用动物的饮食结构来打个比方。
有些动物吃的东西非常特殊。比如大熊猫,只吃那么几种竹子。再比如吸血鬼蝙蝠,只吃活着的哺乳动物的血。别的东西它们一律不吃。这种吃法可能比较省心,它们永远都不用自己判断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不能吃……但是,这是一种把路越走越窄的吃法。
一旦环境变化,比如说没有那几种竹子了,大熊猫可就麻烦了。
我们人类是另一种吃法,我们是杂食动物。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路越走越宽,但是这对你有个更高的要求:你得有判断力才行。比如吃某个东西吃出了毛病,或者你看别人吃出了毛病,你得会长记性,下次碰到这种食物就不吃。
杂食动物的特点,梅西尔称之为“开放的机警(open vigilance)”。一方面你很开放,什么东西都能尝试;另一方面你又很机警,有判断力。而对比之下,单食性动物则是保守而又愚钝的:它们只吃特定的东西,而且哪怕那个东西坏了,它们也不会判断。
梅西尔说,人类的交流方式,也是开放的机警。
动物只能接受有限的几种信号,为了让一个信号可信得花大价钱。我们人类的交流方式很多,语言、表情、动作、抽象符号,我们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交流成本很低,你当面跟我说一件事情也行,你非得用英文给我发个电子邮件也行,我都能相信你!人类交流的开放度非常高。
但是光开放不行,我们还得机警。我敢信任你,是因为有办法能识别信息的真假,完了我可以惩罚你。
人类交流方式的演化,就如同从单食性动物到杂食性动物。你看越是原始部落的人思想越保守,只信任自己的族人,遇到外族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打仗。等到社会越来越复杂,我们可以和陌生人打交道了,甚至可以相信陌生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更精明了,更善于识别谎言。我们没有因为害怕受骗而减少接受信息,社会演变的趋势是人们接收越来越多的信息。
个人也是这样。小孩就相当于是单食性动物,生活在非常有限的环境中,很少跟陌生人交流。小孩很相信父母和老师的话,因为他只能接触这些人。人慢慢长大以后,接触人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开放,思考能力越来越强,人也越来越机警。
横向比较,聪明爱思考的人往往更容易接收新东西。而那些比较笨、不爱思考的人更保守,他们只相信自己以前知道的东西,接触新事物的第一反应是不信。历史上的新思想、各种当时看来是异端邪说的东西,往往都是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普通老百姓是不信的。
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特别容易轻信的人,轻信的物种早就被演化淘汰了。只有两种人能稳定地存活下来:一种是开放而又机警的,一种是保守而又什么都听不进去的。
这一讲我们对比了几种交流方式 ——
第一,没有利益冲突的个体天生就是无障碍交流。比如蜜蜂,因为工蜂是不能生育的,各个工蜂是纯粹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绝对的信任。
第二,如果有利益冲突,就会有问题。比如母子之间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利益冲突,都导致了一场战争。
第三,有效的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比如瞪羚,宁可付出冒险的代价,也要发一个有效的信号。
第四,最高水平的交流,则几乎不需要代价 —— 这就是人类“开放的机警”式的交流。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跟人交流,但是如果科学家不弄一个理论,我们还真说不清自己有什么交流策略。事实上就连科学家一开始也弄错了,这才给了梅西尔一个颠覆主流学说的机会。
这就如同《易经》里说的那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你在用,但是因为你不会总结、或者你总结的不对,你就没法从中学习和提高。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也许就可以从中悟出一点做事的原则 ——
越高水平的交流应该越开放,同时伴随着机警。你要说把门关起来只跟自己人交流,或者只跟认证过的“友好人士”交流,那就不是自信而是畏惧,不是进步而是退化。不管是谁,咱先交流起来,在交流的过程中保持机警,这才是符合天道的做法。
梅西尔总结了四种机警的方法,咱们后面再说。
注释
[1] 博弈论12. 怎样筛选信号
[2] 博弈论6. 布衣竞争,权贵合谋
[3] 《与陌生人交谈》4. “增强审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