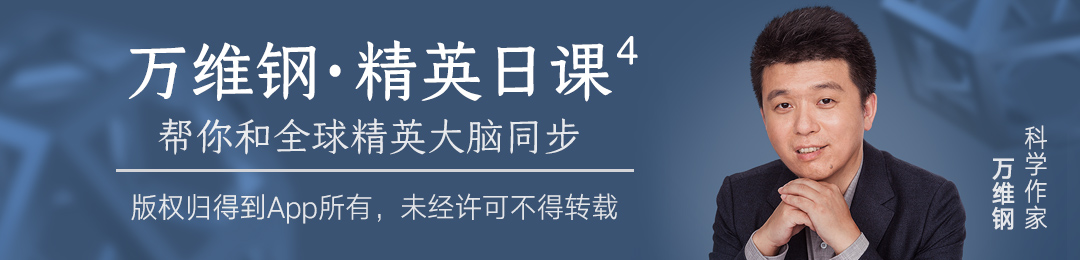你是否注意到,越是大人物说话就越没意思。比如说,假设比尔·盖茨到中国访问,一家主流媒体给搞了个深度访谈,你会特别想看这篇访谈吗?
我完全不好奇盖茨的访谈。他从微软退休以后说的话永远都是这几句:我如何热爱这个世界,我在非洲做了什么什么慈善,我相信科技能改变世界,你们中国很有前途……也许每次用的故事不一样,但姿态永远一样。与其看这样的访谈,我还不如上微博看人吵架。
但盖茨这样的人不可能一直都是这么没意思。他们一开始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不然怎么会成为公众人物呢?
这里面有个普遍的道理。等你成为重要人物,你可能也会变得这么没意思。
这是一个“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的故事。我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版本,主人公是我们专栏非常熟悉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赫拉利,正在变得没意思。
今年二月的一期《纽约客》有一篇关于赫拉利的长篇报道 [1],我读了之后,情绪复杂。
作者伊恩·帕克(Ian Parker)使用了完全写实的手法,只是描写和叙述,几乎不加评论。文章讲了赫拉利从年少求学到成为世界名人的过程,讲了他的工作和生活风格,他对冥想的爱好,他作为同性恋者的感情经历,这些都算正常。但这篇报道中最强烈的信息是,赫拉利现在是一个思想商人。
赫拉利在以色列有个公司,雇佣了十二个人,专门负责推广他的书并且形成周边产品。赫拉利的丈夫同时也是他的经纪人和领导,他的说法是“赫拉利为我工作”。这些人非常精准地营销赫拉利,我看他们简直就是把赫拉利给控制起来了。
他们对赫拉利当前知名度的定位是“麦当娜和史蒂芬·平克之间”。2017 年达沃斯论坛邀请赫拉利出席,赫拉利团队认为给的位置不好拒绝了。2018 年达沃斯论坛安排赫拉利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对谈,他们才同意出席。他们对赫拉利跟谁公开座谈、谈什么非常敏感,但是敏感的不是思想碰撞有没有意思,而是是否有利于获得更大的知名度,是否能维护良好形象。
以及能拿到多少钱。赫拉利参加私人论坛的出场费超过三十万美元,他的公司是个盈利公司。这些其实都无可厚非,让我情绪复杂的是,赫拉利的犀利,好像没有了。
《人类简史》之所以那么流行,是因为这是一本非常犀利的书。赫拉利提出智人的超能力是想象虚构的东西,说农业革命对人的幸福而言是个错误,说小麦驯化了人类,这些思想都引起过争议。在《未来简史》里,赫拉利担心人工智能会夺走人的工作,猜想未来世界会有很多无用之人,“神人”会取代我们智人,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那现在赫拉利有没有什么新的、能让思想震荡的说法呢?没有了。
赫拉利的第三本书,《今日简史》,几乎没有任何新东西。你要问赫拉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三件事儿:核武器、生态环境和技术 —— 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你要问该如何应对这些大问题,赫拉利只会说各国必须联合起来一起解决,我们要专注!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联合起来专注于干啥呢?赫拉利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赫拉利的读者,曾经跟赫拉利有过交流。一个有思想一个有权力,俩人见面聊了什么呢?聊吃素。《人类简史》里有一段描写现代食品工业对动物太残忍了,内塔尼亚胡读了之后决定每个星期一吃素。
赫拉利的团队给他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他对任何敏感议题表态。如果媒体让他谈谈对以色列大选的看法,他绝不会公开支持任何一方 —— 他不能随便花掉自己的信誉。
赫拉利一直鼓吹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但是这完全不妨碍他去硅谷各大公司演讲。他会说一些模棱两可没有营养的话,不想让 Google 们把自己视为敌人。他曾经激烈批评 Facebook 控制人的思想,但是这不妨碍他去扎克伯格家里做客,然后说“我认为扎克伯格不是个邪恶的人”。
但是赫拉利坚持了自己的论点。他的最新说法是两百年后就不会再有智人了。而正在掌握更多数据的中国,是他的最新假想敌。
帕克问赫拉利,那我们作为个人,该怎么办呢?他说冥想。
我并不反对冥想。我们专栏详细介绍过赫拉利的论点,但是我们也从别的角度考察过相关的议题。我们多次讲到,人工智能技术远远不是外行想象的那样,本质上都是机器学习,非常笨拙,应该叫“人工不智能”。我们还讲了,用基因工程创造新人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演化已经把人的基因调节的很好了,而且像智商这样的功能往往都有数十个基因共同起作用,根本就没法调……
赫拉利了解这些知识吗?我没看出来。帕克倒是在报道中对赫拉利的物理知识有一次吐槽。赫拉利跟帕克聊到信仰的力量,说信仰就好像物理学中的“弱力” —— 虽然弱,但却是把原子核凝聚起来的力量。可是赫拉利说错了!把原子核凝聚起来的力量是“强力”,弱力其实是让原子核*分裂*的力量。
赫拉利有一个团队,史蒂芬·平克只有一个出版经纪人和一个演讲经纪人,但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这些明星学者就好像艺人一样到处参加活动。平克说有些活动是太有意思了,有些活动是太赚钱了,这两种他都不能拒绝。
赫拉利和平克联合做过一期电视节目。观众期待的是思想碰撞 —— 节目的设定正是如此,两人一个扮演技术进步的支持者一个扮演反对者。但他们不会在辩论中真打起来,因为他们都明白这是节目。
我们专栏介绍过的“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是这两年新近崛起的明星学者,他也曾经试图跟赫拉利约一场辩论节目,被赫拉利团队否决了。团队担心跟彼得森辩论会陷入混战,影响赫拉利的品牌形象。
是的,赫拉利和平克这帮人,已经从学者变成了品牌。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要为思想负责,而且还要为很多人负责。如果你要为人负责,你就会变得没意思。
你会越来越被自己的“立场”所束缚。
普通人 —— 比如中国网民 —— 喜欢表达立场。比如说最近中国运动员孙杨被禁赛八年这个事件,有的人一听就立即表态支持孙杨:孙杨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要支持中国人。立场表达让他有了存在感,他也许会为了表达立场而去寻找一点论据,但是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有没有技术含量。
而普通人的立场又很容易改变。等到事件的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他发现原来当事人居然做出那样的事情,那我肯定反对他:我是聪明的好人,聪明的好人不跟愚蠢的人站一起。他的立场经常反转。
如果你把立场比喻成爱情,普通网友的爱情是浅薄的。他们动不动就表白,可以对任何人表白,但是也只有表白。
而大人物,把立场视为婚姻。他们会用各种科学有力的观点去经营自己的立场。他们哪怕在内心对某个议题倾向于某个立场,也绝不会轻易表达出来:因为离婚的代价太大了。
比如你说你是个进步主义者,你出了好几本书赞美技术进步,你有很多粉丝,比尔·盖茨说你的一本书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
那你能说,哎呀,我跟赫拉利对话之后,觉得还是他说得对,我宣布改变立场,我以前写的书都有问题……吗?你让粉丝和比尔·盖茨情何以堪。
不但不能改变立场,而且还必须时刻重申原有的立场,因为你是一个品牌。对赫拉利的公司来说,指望赫拉利每年出一本书给老读者提供新鲜刺激是困难的,但是开拓新读者似乎更容易一些。公司正在开发《人类简史》的青少年版、少儿漫画版和电视纪录片版。
而这些都要求赫拉利在每一个场合重复宣讲他以前的论点。代价是让老读者感觉他变得没意思了。
我们喜欢的“有意思”,是一种先锋感。或者是对一个敏感的议题大胆提出一个鲜明的立场,或者是突破自我,改变人们熟悉的立场。这两件事都不适合成熟的思想品牌去做,可是难道“思想品牌”,不就得经常提出新思想才行吗?
这是一个悖论。我看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罗杰·马丁(Roger Martin)教授曾经有一个关于智库的说法 [2],说一切智库都面临着“新”和“对”之间的悖论。
按理说,作为一个智库,你的价值是给人提供新思想。可是新思想常常有可能是错的 —— 特别是关于社会问题,你又不能先拿社会做个实验,创造性的想法都得大胆尝试一下才知道对不对。企业或者政府要购买你的服务,必然要求你给提供一个正确的建议 —— 可是正确的建议往往不新,你不说别人也知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库能改变的事情极其有限。
赫拉利的公司也打算升级成为“智库”,给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可是赫拉利现在对任何问题都不敢提出具体的建议 —— 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具体建议,我们需要这样的智库吗?
赫拉利和平克这样的人,遵循一个古老的命运。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只有一身本领而没有任何负担,他们可以大胆打碎一个旧世界。他们是屠龙的少年。如果冒险成功,他们就能建立自己的名望和地盘。
可是有了名望和地盘,他们就不得不维护这些东西。他们发现自我重复比自我更新容易得多,发展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新创,大人物的玩法是强强联合而不是互相攻击。他们变得小心谨慎,不愿意、也没必要再去冒险。
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当上了领导,学会了对任何事物都不表态的道理。他们永远只在大局已定的时候才做总结性发言。而殊不知,当他们从一个演讲走向另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已经不再有意思了。当初屠龙的少年,已经变成了恶龙。
屠龙的少年变成恶龙,创新者遭遇窘境,明星学者的立场失去悬念,这些故事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革命者会反对新的革命。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年轻人才永远有机会。我们会在下周开始的《量子力学》课程中再次看到这样的故事。
注释
[1] Ian Parker, The Really Big Picture, The New Yorker, Feb. 17 & 24, 2020.
[2] Roger Martin: The Paradox of Think Tank Innovation, Keynote, CIGI 1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September 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pqewOx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