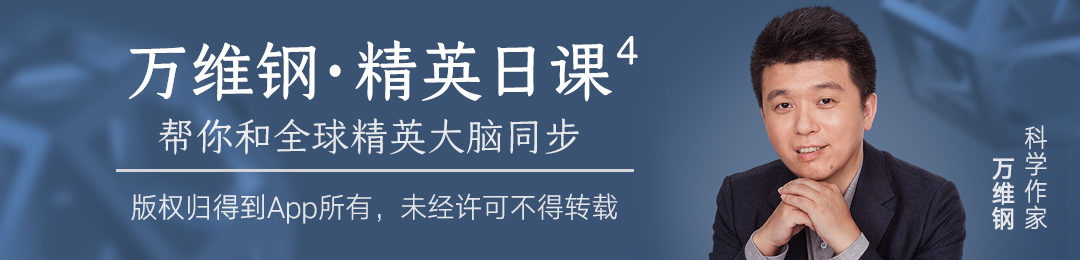这是丹·希思《上游》这本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说说上游思维有多难。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进京赶考,情绪高涨之下写了一首诗 ——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
哪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
几人从此到瀛洲!
这首诗不但是意气风发,而且有我行我上、舍我其谁的气魄。其实每一个中国读书人都有想要建功立业的情怀。我们读书就是要救国救民,要改变世界。年轻人读书要是没读出这种感觉,那你白读了。士,就得有这样的劲头。
而你会面临各种难题。你可能说我不怕难题!我能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实在不行我还可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 —— 有敌人我就要战胜敌人,贪官污吏敢阻挡我我就要跟他们斗争!
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要说的困难,还不是这种困难。有敌人的时候,至少你的方向是明确的,你完全知道该干什么,可能只是力量不够。
真正做事的人,苦恼的不是这些。
1.灾难时刻
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数千人的死亡,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而政府的救灾行动,简直是国家的耻辱。人们都说这个灾难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先就有人发出过多次的警告,甚至就在灾难发生的不久之前,政府还专门组织过一次演习……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警告你们都当耳旁风了吗?你们演习都演习什么了呢?
我说的可不是新冠病毒。我说的是2005年,发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州的卡特里娜飓风。
专家早就知道新奥尔良的堤坝不安全。在飓风发生之前,美国政府还专门给了一个叫做“创新应急管理(Innova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IEM))”的私人公司80万美元的经费,让它制定了一个一旦发生飓风,新奥尔良地区应该如何救灾的计划。
你可别小看这种私人公司,它们的水平往往比官方机构高,像 IEM 就是一个研究型的智库。事后证明,IEM 简直是无比精确地预测了飓风灾难的过程:包括降雨量、水位、有多少人需要转移、有多少人会面临停电等等,它预测的数据和真实结果相差居然不到10%。
而且当地政府也不能说完全忽略了 IEM 的预测。就在灾难发生之前不到一年的时候,州政府就组织过一次灾难演习。
那为什么救灾还是失败了呢?为什么还是死了那么多人呢?
也许答案是……本来会更失败。
灾难的过程几乎跟 IEM 的预测一样,只有一个关键差别,那就是死亡人数。卡特里娜飓风实际导致了 1700 人死亡 —— 而 IEM 当初的预测,是死亡 6 万人。
也许你应该感慨的不是为什么居然死了 1700 人,而是为什么少死了 58300 人。
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那次演习。演习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把离开灾区的一条高速公路从双向改成单向,也就是说把左右两条路都设置成出城的路,这样尽量让更多群众转移。这个说着简单,实际操作有很多难点。你需要把各个反向的路口都封上,要指导灾民从哪上路,要发放很多地图,而且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演习中灾民喜欢停车问警察前边怎么回事,警察都耐心讲解 —— 演习结束后总结经验,这个太耽误时间了,于是改成警察只做手势让人赶紧往前走,不许停车……
正是因为有过这次演习,灾难中才成功转移了120万人,总死亡人数才从 6 万人变成了1700人。
然而事后再说这些都没用。人们只会抱怨救灾不力,没有人会在乎你当初在上游有过什么行动。灾难中没有功臣。
那你说如果你的工作做得特别好,以至于把灾难给完全避免了,那会怎么样呢?你还是没有功劳。
2000年之前,很多人担心所谓“千年虫”的问题。以前的程序员为了节省宝贵的存储,把比如说“1995”年都缩写成“95”年 —— 只用两个数字代表一个年份,而这就是带来了隐患。2000年,老式计算机会写成“00”,这算是1900年还是2000年?人们担心这会导致银行和政府的系统崩溃。
克林顿政府专门指定了一个专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避免千年虫。专家组做了很多工作。最后2000年 1 月 1 日这一天,全世界只有一点小小的波折,基本上平安度过。
好,那你说,这算不算专家立功了呢?没有。事后人们纷纷发表评论,说所谓“千年虫”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噱头,甚至是一个骗局!专家组有口难辩。
其实现在你要问我“千年虫”到底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在上游做事就得接受这样的结局,没人知道你到底起没起作用。
在下游救起孩子、力挽狂澜,你会收获掌声和荣誉;上游通常没有这种胜利时刻。做得特别好,你就是一个无名英雄;而如果你做了但是灾难还是发生了,你还会受到指责。
绝大多数公共事务没法做随机实验。没有人知道,在那个没有你的平行宇宙里,发生了什么跟我们这里不一样的结局。
就算有随机实验,其实也不容易。
2.随机实验的难处
所谓随机实验,就是把受助者分成两组,实验组我们在上游做一下干预,对照组不干预,然后看看结果,实验组的境遇是不是比对照组好,就能证明那个上游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这么说很简单,实际操作中你会有很多纠结。
比如我们前面讲了芝加哥市为了降低青少年的犯罪率,搞了个叫做“成为男人(Becoming A Man)”的心理辅导项目。2009-2010 这一年中,项目组在 18 个高中里分别给学生上了 27 堂课。但是结果出来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
心理辅导不是万能的。老师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生中仍然有人去参与暴力活动,有人被抓起来了,甚至还有一个学生被枪杀了。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做的有没有意义。项目结束后又过了九个月,芝加哥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才拿出随机实验的对比结果。结果是实验组的各项数据大大好于对照组。项目创始人说,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如果能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有意义,你真是应该感到无比幸运。有多少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他的学生中有优秀的人才也有犯罪分子,而他永远都不知道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其中多少人 —— 他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改变过人。
而拿到那个证明很不容易。随机实验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上一讲说的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护士-家庭结对关系”(NFP)项目,在整个实验的六年之中,医护人员完全看不到数据。你知道这个实验最残忍的是什么吗?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在这整整六年中,医护人员都不允许学习新的护理方法。
你不能有任何创新。你说你出于好意,想多帮助受助女性一点,那绝对不允许。你只能重复使用老一套的标准做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拿到最干净的数据。
而就算实验结果明确证明了你这个方法有效,能不能大规模推广还是一个问题。
比如“成为男人”这个项目,后来又做了更大规模的随机实验,效果就比之前的小范围实验弱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保证质量。
在芝加哥市找13个热衷于帮助青少年的人很容易,但你想要找130个、1300个就没那么容易了。社会服务跟开麦当劳连锁店不一样。麦当劳能确保所有连锁店的炸鸡味道都一样,而你把操作流程弄得再规范,这也不是炸鸡。你的教学方法再高明,没有好老师也不行。
如果“护士-家庭结对关系”真的有那么好,那政府干脆多花点钱,给每一个贫困家庭都配上一个医护人员行不行?你找不到这么多的好医护人员。
“规模问题(scaling problem)”,困扰整个学界。几乎所有社会项目都是这样的宿命:小范围实验结果特别好,一推广就不行。
3.什么使命?
那我们再退一步,假设有个项目不但有效,而且也能够推广。那你以为这个项目就可以推广了吗?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CMS)有一个基层官员,名叫达尔沙克·桑哈维(Darshak Sanghavi)。他的任务是寻找那些使用了上游思维、能帮医保省钱的创新方法。
桑哈维关注了一个预防糖尿病的项目。这个做法是用数据分析找出那些没有得糖尿病、但可能得糖尿病的高危人群,由政府出钱给他们请教练,让他们到社区去参加锻炼课程。要求的锻炼并不难,只要每周有 2.5 小时的体育运动就行,哪怕散步都可以,并且要把体重降低5%。
随机实验证明这个项目管用。实验组得II型糖尿病的概率比对照组少1/3,而且即使后来得了糖尿病,也把得病的时间推迟了4年。也就是说每个人至少多了四年的健康生活,这非常好,对吧?
2015 年,桑哈维申请推广这个项目,但 CMS 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你可能难以置信 ——理由是这项目一旦实行后,高危人群的寿命就会延长 ,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花掉更多的医保支出!
桑哈维简直出离愤怒!政府竟然为了省钱,而不想让国民活得更长!什么叫万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桑哈维冷静下来以后,给 CMS 高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最后是这么说的。医学道德的第一条,就是“不伤害”,医生是这样,我们所有这些跟医疗相关的人员也应当如此……所以,CMS 的条例必须加一条,规定不能把延长人的寿命而多带来的花费,作为可以考虑节省的开支。
事情的结局还可以,CMS 还真把这一条写进去了。
希思没有说那个预防糖尿病的项目最后有没有获得政府支持,但是桑哈维的胜利比一个项目更有意义。因为他的坚持,以后可能不会再有类似的项目,因为如此残忍的原因而被拒绝。这个胜利没有掌声也没有荣誉,但是非常重要。
这就是上游思维的难处。社会可能会误解你,上级可能不支持你,很多时候,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这里面没有多少直来直去的简单问题,没有多少英雄式的痛痛快快的成功,这里面的故事没有完美结局。
想要在这样的世界里负点责任,你有时候不但不能指望功劳,还得有背黑锅的觉悟。《马关条约》一签,李鸿章立即成了卖国贼。这时候你要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可能更差……会有人听吗?
《上游》这本书就算给你讲完了。最后咱们再来读一首李鸿章死后,有人假托他的名义写的诗。跟开头那首正好是个对比,似乎更能体现上游思维 ——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The End)